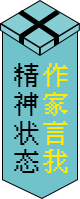-
>
我与父辈(九品)
-
>
商市街 回忆鲁迅先生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彩虹几度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古都·虹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舞姬·再婚者
-
>
碧轩吟稿
-
>
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第三辑)(全十五册)
意大利的黄昏 版权信息
- ISBN:9787532769384
- 条形码:9787532769384 ; 978-7-5327-6938-4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意大利的黄昏 本书特色
劳伦斯的首部域外游记,见证了他与意大利的初次相遇。
2015年恰逢劳伦斯诞生130周年。
在劳伦斯笔下,欧洲乡间美景跃然纸上,静谧、宁静的湖光山色带给他关于人性与现代文明的思考。
本书是目前市面上仅有的劳伦斯游记单行本。
意大利的黄昏 内容简介
本书是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一部域外游记,也是其*知名的一部游记作品。劳伦斯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和意大利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四海为家的人生中,总共有三段旅居意大利的经验:一战爆发前在加尔达湖区,一战结束后在西西里岛,以及晚年养病在佛罗伦萨。《意大利的黄昏》是劳伦斯的**部域外游记,见证了他与意大利的初次相遇,也记录了作者在旅途和客居期间的种种见闻与感思。
意大利的黄昏意大利的黄昏 前言
黄昏里的羁旅(代译序)
劳伦斯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和意大利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四海为家的人生中,总共有三段旅居意大利的经验:一战爆发前在加尔达湖区(1912年—1913年),一战结束后在西西里岛(1919年—1922年),以及晚年养病在佛罗伦萨(1925年—1927年)。《意大利的黄昏》是劳伦斯的**部域外游记,见证了他与意大利的初次相遇,也记录了作者在旅途和客居期间的种种见闻与感思。
话说重头,劳伦斯与意大利的缘分还得回溯到1912年。那年4月的某天,他应邀参加了一场家庭餐会,而设宴的正是他原先在诺丁汉大学的法语教授威克利。那时候,劳伦斯仍未走出丧母之痛,而感情生活又颇多纠葛,加之肺病二度来袭,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他*潦倒、*失意的人生低潮。然而,就在那次餐会上,女主人的出现似乎让他的生活瞬间发生了逆转。弗里达威克利,出生于德国的贵族家庭,20岁那年远嫁到英国,她与教授结婚12年,育有二女一男。相比之下,劳伦斯非但出身卑微,而且27岁的他还比弗里达年幼5岁。 然而,就是这一眼之缘,立刻点燃了爱情的熊熊火焰。又过了三个星期,两人便开始策划私奔。5月3日的下午,这对叛逆的爱侣怀着忐忑又兴奋的心情,怀揣着仅有的11英镑,坐船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弗里达打算直奔德国老家梅斯,将这重大决定告诉家人,顺便参加父亲军旅生涯50周年的庆典。5月7日,劳伦斯和弗里达在梅斯镇上闲逛,不料竟被当地军方扣押,罪名是私闯军事设施、意图窃取情报。不过,所幸弗里达的父亲德高望重,经他的求情,劳伦斯于次日即被释放。可是,既然已有英国间谍的嫌疑,劳伦斯决定还是暂且离开这是非之地。然而,热恋中的男女到底经不住相思的煎熬,于是,不久两人又在慕尼黑重聚了。为了节省费用,他们在城郊租下了一间小套房,共度了天堂般美好的一段蜜月。可是,这样的日子毕竟过得太清苦。他们省吃俭用,两个月花费还不到10英镑,可仍然入不敷出。于是,在弗里达姐姐的建议下,两人毅然决定移居到生活费用较低的意大利。
8月5日,他们踏上了漫无目的的旅程;他们只知道一直向南,因为据说阿尔卑斯山的南麓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劳伦斯和弗里达将三箱行李先行托运到奥地利南部的里瓦,而自己则打算徒步旅行。两人从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出发,一路上翻山越岭,遭遇了各种恶劣天气:饿了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小酒精炉,胡乱煮些吃的聊以果腹;困了就找间干草棚倒地而眠。好几次,弗里达实在受不了那委屈和折磨,两人也会坐一趟火车。然而,艰辛的旅途也一样给他们带来了惊喜。在荒废的古驿道上,在山顶积雪的映照下,沿路的十字架与基督像渐次映入了眼帘。在巴伐利亚,它们的模样陈旧、灰暗又抽象,基督则完全是德国农夫的模样。他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躯体仍旧完美、贞定,成就了其永恒的存在。沿着伊萨尔河溯流而上,奥地利境内的十字架大多更为硕大、醒目,基督的面部和身体在在表现出极致的痛楚和完全的死。在这里,基督象征着死亡的幻灭与终结,而他的雕像也折射出人们对死神与痛苦手段的崇拜。再翻过阿尔卑斯山绝顶的关隘,进入南麓的蒂罗尔山区,这里的基督像更为多样:有的姿态优雅,在十字架上表现出自豪与满足;有的则纤弱而感伤;还有的毫不掩饰肢体的伤残,脸上甚至露出忿恨的表情。凡此种种,无不引发劳伦斯的思考:何谓存在?永恒的存在与人世究竟有何关联?夏日的某个午后,山里突然下起雷阵雨,劳伦斯目睹主人一家如何匆忙将铺晒的干草抱回草棚。冰冷的雨水浇淋在劲健、温热的身体上,干草的暖香则由怀中沁入到心脾。“这是十分愉悦的体验,是各种身体感受火热的交融。它让人心驰神醉,就像吞食了催眠的仙丹……”似乎就在这一刻,他感受和领悟到了存在的根基:艺术、宗教和劳动,人世的一切全都基于感性经验;生命是体温,是热血,是肉体的感知,理性与智识也无可替代。而这所谓的血性意识,除了驿道两旁的基督像,在山里还有它对应的自然象征–山巅的皑皑白雪以及它在天心投射的辉光和异彩。那是恒常不变的存在,人生与世间的一切经验无不向着它涌动、变幻。劳伦斯后来将这段旅程记录下来,一共写了七篇札记,其中“蒂罗尔的基督像”改名为“山间的十字架”后收入了本书。
翻越过重重高峰与道道关隘,劳伦斯和弗里达终于进入了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目的地意大利已经遥遥在望。有一天,他们来到奥地利南部的特伦托,在街上看见一张加尔达湖的旅游海报,瞬间就为画中的美景所倾倒,于是两人当即买了一本意大利语词典,跳上火车赶赴行李的所在地里瓦。8月26日,他们顺利到达里瓦,为期三周的艰难征程终于划上了句号。然而,两人携带的23英镑旅费此时已只剩下了一英镑。他们在当地的廉价客栈租了个房间。因为手头实在拮据,两人只好用自带的酒精炉偷偷在屋里做饭。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无力支付低廉的房租,于是两周以后,只好搬出客栈、继续南下,到意大利北部的农村里寻找落脚的地方。劳伦斯四下打听,据说加尔达湖西岸倒是有座名叫加尔尼亚诺的小村,那里房租很低,又依山傍水,实为休养栖息的好所在,只可惜地处偏僻,且仅有水路相通。不过,穷途末路的劳伦斯和弗里达也顾不得这些了;他们只想尽快给自己找个安宁的爱巢,开始新的生活。于是,9月10日,两人满怀希望乘坐汽船来到了这里。加尔尼亚诺果然风光秀丽,近乎于天堂:湛蓝的加尔达湖近在眼前,巍峨的巴尔多山矗立在对岸,如此雪峰、大湖相映成趣,尽得自然之妙。因为月租只要3个基尼,于是他们便慨然在附近租下了一座花园别墅的一层。
这座“宝琳宫”的主人名叫彼得罗,是个家道中落的乡绅。他贪婪、骄矜,可是面对世道的衰微却又无可奈何。夫人婕玛也是德国裔,比他年轻许多,可是,两人结婚多年并未生儿育女,感情上早已貌合神离。一条松弛的美国专利门弹簧、一扇怎么也合不拢的大门,不但暴露了旧世界面对现代文明入侵的窘境,同时也象征了两性关系的挑战与危机。尤其是意大利人对孩子的敬爱,在劳伦斯的眼里,几乎是一种倒错的阳具崇拜。在“柠檬园”一文里,劳伦斯几乎是跳跃性地联想到了所谓意大利之魂的问题。通过爬梳中世纪以降的精神史,比较欧陆南北的文化传统,他概括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无限观”:异教的(如意大利)和基督教的(如英国)。前者以米开朗基罗为典型,认为感官和肉体是可以自足的目标,强调感性体验的绝对性和神圣性。它标举绝对的自我意识,冀望在感官的极致满足中“出神入化”、达致无限自由的境界。而后者则以耶稣基督为代表,认为完满的无限与自由全在于“非我”,强调对自我的否定,主张摧毁私我的所谓神圣性。它标举大写的我,所以特别勉力于科技的发展与社会革新,冀望以此谋求*大范围的公益与慈善。根据劳伦斯的观察,南北欧正因为理路的不同,于是便发展出了迥异的社会与文化形态。而意大利若要去尽它那暗沉、阴郁的底色,就必先经过自我否定的洗礼。这将是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但劳伦斯认为,藉由圣灵的帮助,它可以突破自我,*终与基督教的无限观整合归一。
劳伦斯出生于英国中部的矿区,从小就熏染了工业化的滚滚浓烟,对此他终生都深恶痛绝。相比之下,眼前的加尔达湖简直就像一片世外桃源:山明水秀,民风淳朴。然而,就在这貌似前工业化的旧世界里,在这人迹罕至的角落里,文明与传统似乎也露出了黄昏的微熹。曾几何时,山坡上的柠檬园是当地农民与乡绅(包括劳伦斯的房东彼得罗)的希望和骄傲,然而,当机器文明席卷全球的时候,农民渐渐远离家园,走进城里的工厂,开始为资本家卖命。于是,那些柠檬园不是永远地废弃,就是挂出了转让的牌子。劳伦斯看到,人们似乎不再珍惜和煦的南欧阳光,这上帝赐予意大利的特别赠礼。他忧心,意大利正在步英国的后尘,想要借助机器征服世界、实现自我,又或者是自我的迷失或毁灭。
文明的黄昏不但降临到荒凉的山坡上,同时,也照进了所有村民的心里。劳伦斯在加尔尼亚诺居住了半年,他观察和结识了村里村外的各色人物。“纺妇与僧侣”或许是其中唯一能够置身世外的异数。教堂外面,高台上的老妪自顾自纺线,几乎完全无视我的存在。劳伦斯发现,“她像一块泥土,一块鲜活的石头,在高台上被晒得煞白。”她的世界里没有自我与他者的分别,一切通透澄明;现代人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她的世界里荡然无存。如果说纺妇的身上体现了矛盾的缺失,那么,两名僧侣则似乎在努力调和矛盾。他们徘徊在昼夜、昏晓之间,不偏不倚,中正允执,恰似夕阳里山顶那玫红的积雪,即代表无上的超越与恒常,又展露尘世的欢颜与喜悦。
然而,其他人的生活则多少受到了机器文明的冲击,或者暴露出意大利传统文化的沉疴与痼疾。困在里面的人,或者苦闷、彷徨,或者软弱、无助。有一天,劳伦斯受邀去邻村看戏。他发现,台下的男女居然全都分坐剧场的两边,而不是阖家共赏、尽享天伦。夫妻间似乎只剩下猜忌、暗斗与敌视。要不是孩子,他们的婚姻几乎已经名存实亡。表面上,在两性的战争中,女人像是占了上风。然而,咄咄逼人的她们却也叫失势的男性感到委屈、耻辱和无能。于是,男人只好把自己灌醉,或者回家打老婆,要不然就选择逃离。当然,也有人将这苦闷表现在了舞台上,譬如那个巡回剧团的领班和主演恩里科佩瑟瓦利。这个男人台上台下一样地张扬得意,但劳伦斯一眼就看出他灵魂的软弱,甚至将他比拟为现代的哈姆雷特。劳伦斯认为,二者的身上同样表现出强烈的自厌倾向。当文艺复兴运动一举摧毁了帝王贵族的肉体神性之后,意大利人便转而冀望在自我感官的极致满足中获得喜乐与自由,而这在劳伦斯看来,显然正是意大利人一切苦难的渊薮。他们执着于古希腊人的异教式无限观,不愿像北部的民族放下肉身、舍弃自我,不愿历经身体的死亡来重获新生。几百年后,“是生存,还是毁灭”,舞台上佩瑟瓦利扮演的哈姆雷特仍在这样叩问自己的灵魂。
劳伦斯和弗里达在加尔尼亚诺居住了六个月,在这里度过了*寒冷的日子。其间,他们接待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好友安东尼娅阿尔格伦(即“舞”中那个黝黑的英国女人)。安东尼娅定居在一座名叫圣高登齐奥的农庄。劳伦斯和弗里达也想搬到农庄同住,可是碍于眼前的租约仍未到期,所以只好等到1913年3月下旬才如愿以偿。因为要回英国,其实他们在圣高登齐奥也就住了两周。然而,农庄主和他的家人仍旧给劳伦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男女主人保罗和玛利亚,在生养了三个子女以后,在经过多年的激烈争吵以后,终于可以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安无事。然而,劳伦斯也看出来了,这迥异的两个灵魂其实更像宇宙的两极,静默而疏离。反观自己,他和弗里达之间同样充满了明争暗斗,两人尚未稳定的关系仍叫他忧心忡忡。在圣高登齐奥,他认识了缄默的保罗、神秘的“硬汉”、懵懂的约翰,还有即将长大成人的保罗之子乔瓦尼。除了装着义肢的樵夫,似乎这里的每个男人都在选择逃离,逃离到远隔重洋的美国。保罗的出走是为了逃避无奈的婚后生活,可到头来,那不过就是一场“心灵的梦游”。在责任感与旧观念的驱使下,他*终还是回到了家园–做一个守护农庄的幽灵。而年轻一辈的约翰、乔瓦尼,他们对故土再无任何留恋;他们只想远走高飞,却又不知去往何处,于是,便把那命运所指的方向含糊地叫做“美国”。
在外漂泊太久的人终归会想家。1913年4月,劳伦斯和弗里达离开加尔达湖,来到慕尼黑。在郊外别墅小住一个多月后,两人终于回到英国。令劳伦斯十分欣喜的是,新近出版的小说《儿子与情人》大获好评,与此同时,一份不算丰厚的稿费也让他的生活多少有所改善。而弗里达则没有那么幸运:丈夫威克利再度坚拒了她的离婚要求,甚至阻挠她与亲生骨肉相见。同年8月,两人启程重返欧陆。9月中旬,在慕尼黑期间,弗里达得知父亲病重,便立即奔赴巴登探望。与此同时,劳伦斯决定再来一次徒步旅行,即由德国出发,穿越瑞士全境,抵达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意大利,并*终与弗里达在米兰会合。
劳伦斯花费了两周的时间,才走完这段孤独而艰辛的旅程。然而,他却亲昵地将这次跋涉称之为“归途”。他甚至固执地认为,所有愉快的旅程必定是向着南方或西方的。此时,在劳伦斯的心目中,意大利已不再只是个能唤起种种美好联想的地理名词–阳光充沛、景色怡人;它更像个可以安顿生命的精神家园、抚慰心灵的收容所。然而,旅途的见闻却告诉劳伦斯,还有太多的灵魂仍然漂泊在外,或者迷失在路上。譬如他在瑞士客栈里偶遇的这些意大利人。他们为了躲避兵役和赋税,陆续逃离了故乡,栖身在阴寒、闭塞的瑞士山谷里,相依为命。他们仍然怀念故国,怀念那里的风物和艳阳。但是,这深深的思念里却又交织着难言的哀痛与鄙夷。劳伦斯为这些永失家园的“孩子们”感到神伤,他甚至无法念及这些人,因为“只要回忆一触及他们,我整个灵魂就停摆了,失效了,无法继续。”而另一些灵魂则在现代机械生活的压榨下苦不堪言。于是,短暂的自我放逐便成为一种纾解压力的方式。那个即将入伍服役的里昂青年,那个暴走自虐的伦敦文员,那个少不更事的巴塞尔小伙儿……文明世界恩赐的一周或两周的假期,不过是一条栓狗的皮带;他们终究还要回到那非人的大机器里去。
如果说来时的路–荒废的古驿道–让劳伦斯见识了欧洲传统曾经的辉煌与力量,那么,这段归途则一步步证实了他的担忧。即便在欧洲的内陆,机械化也已迅速渗透至每个角落。瑞士的山谷里,工厂的浓烟熏黑了人们的灵魂。山顶的小镇居然也充斥着游客和广告牌。劳伦斯把这喧嚣、混乱的世界比作一辆翻倒在路边的搬运车,“各种大件家具倾泻而出,可是谁也不来收拾。”更让他触目惊心的则是那些公路:宽阔、崭新,却又污秽至极;驿道两旁的十字架在这里被大楼和厂房代替。劳伦斯意识到,旧秩序正在脆裂、腐坏,一路由黄昏坠入黑夜。即便在米兰广场涌动的人潮中,他都能嗅到机器文明发出的恶臭。
《意大利的黄昏》共收录札记十篇,其中“山中的十字架”(原名“蒂罗尔的基督像”)写于1912年9月至1913年3月。“纺妇与僧侣”、“柠檬园”、“看戏”等三篇则是1913年冬天在加尔尼亚诺完成,并于同年9月登载于知名杂志《英国评论》。上述四篇在集结出书前都曾做过大幅修改。而余下的六篇文章则都是一战爆发后,即1915年9、10月间作者在英国补写的。劳伦斯一般将这十篇札记统称为《意大利忆往》(Italian Days),后出版社将其更名为《意大利的黄昏》,并于1916年6月1日正式刊行。
《意大利的黄昏》虽是一本小书,但译者和编辑并不因此轻忽、松懈。感谢译文出版社顾真先生的信任、鼓励与支持。感谢让我再度踏上翻译这妙不可言的旅程。当然,译文中的任何纰漏,也必须由译者一人负责、承担。
刘 志 刚
2014年6月16日于杭州
意大利的黄昏 目录
山间的十字架
加尔达湖
一、 纺妇与僧侣
二、柠檬园
三、看戏
四、圣高登齐奥
五、舞
六、“硬汉”
七、约翰
漂泊的异乡人
归途
意大利的黄昏 节选
通往意大利的古驿道始于慕尼黑。它纵贯蒂罗尔山区 ,途经因斯布鲁克 与博岑 ,再越过几重山脉,便可抵达维罗纳。曾几何时,德国的商队跟随着皇帝,浩浩荡荡由此南行,又或者从蔷薇花开的意大利踏上漫漫的归途。
而今,昔日帝国的繁华,在德意志的灵魂里尚余几何?德国君王是否仰承了罗马帝国的遗绪?这虽然不是个十分真实的帝国,但其声势却曾是那么炽盛而辉煌。
或许,妄自尊大本来就是德国人的天性。倘若每个民族都能了解自身的特性,倘若他们可以彼此了解、和谐共处,事情该会是多么简单啊。
如今,再也见不到帝国的商队翻山越岭,向南而行。曾经热闹的驿道几已为人所淡忘。然而,路终究还在那里,路牌也始终未曾摇落。
十字架依然挺立着。它们不仅是指示的路标,更与这驿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想当年,帝国的商队领受了教皇的祝福,然后由大主教一路陪同,在山间竖起这些崇拜的圣物,就如同栽下一株株新苗。后来,它们又因着不同的土壤和民族繁衍、生长。
穿行于巴伐利亚的高地和丘陵,你很快就会发现这里独特的风土,还有那奇异的宗教。这是个非同寻常的所在,偏僻、闭塞。或许,它正是当年帝国商队栖居的地方。
明净、宽阔的驿道一直延伸到山里。一路上,你很少会注意那些十字架和庙宇。也许是人们已经彻底失去了兴趣。十字架本身是空洞的,是一件感伤的工业制品,灵魂漠视它。
但渐渐地,在护罩的掩映下,影影绰绰的十字架似乎营造出一种新的氛围,一种黑暗,笼罩了四野。皑皑的雪光从山上映照下来,空气变得透亮而稀薄,黑暗紧紧压迫着地面。那光亮如此通透而稀薄,从山间泄露出来,焕发出奇异的光辉。此后,在宽阔而草木繁盛的路口,十字架还会不时重现;它们在尖耸的护罩下凝住了一点暗影与神秘。
有天傍晚,我独自漫步于山脚的一片沼地。眼见天色虚淡、澄澈,浑然不似人间,而眼前的山峦却已近乎黢黑,这时我突然惊醒。岔路口竖着一座十字架,基督的足间有一抔枯萎的罂粟花。我先看见花,然后才看见了基督。
那是座旧时的神龛,一尊巴伐利亚农民的木雕塑像。基督曾是阿尔卑斯山下的一名农夫。他有宽阔的颧骨、健壮的四肢。他素朴、平凡的脸膛凝视着前方的山峦,脖颈已然僵硬,仿佛在抗拒那无法挣脱的铁钉与十架。他的灵魂被铁钉压迫着,但他却仍在与枷锁和耻辱抗争。这是个中年男子,平凡、质朴,身上既有农民的刻薄与悭吝,又显出一种不屈的执拗与高贵。这平凡近乎虚空的灵魂,这十架上的中年农夫,他拒绝去除身上承受的苦厄。他不屈服。他的精神不坠,他的意志坚定。他就是他自己,任凭境遇如何,他的生命矢志不移。
隔着沼地有一小方块橙黄的灯光,从低矮、平坦的农舍中透射出来。我记得,那主人和他的妻儿整日辛劳,从天亮到天黑,沉默、专注,将干草从滂沱的雷雨中抱回草棚,然后继续在涔涔的雨里默默劳作。
俯身面朝大地,全身团成一个圈;蜷曲的双臂抱着满怀的干草,干草轻贴着胸口和身躯,将太阳的温暖扎进胳膊和胸口,将干枯的草香沁入心脾。瓢泼的大雨淋湿了肩膀,衬衫紧贴着火热、紧绷的皮肤,冰冷的雨水落在劲健的身体上,畅快淋漓。然后,它们又化作水滴,悄悄流向腰窝和背脊。这是十分愉悦的经验,是各种生理感受的火热交融。它让人心驰神醉,就像吞下了催眠的仙丹:在雨中抱起重物,穿过滋长的草丛,蹒跚来到草棚,卸下满怀的负重,将干草堆积成垛,在干爽的屋里感受轻松自由,然后再回到冰冷的大雨中,再俯身任由雨水浇淋,再起身携重物回到草棚。
正是这,这无尽的火热与觉醒,让身体始终充盈、蓬勃,让心灵充满血的热度与安眠。而这血的安眠,这身体经验的热,久而久之便化为一副枷锁,并*终铸成一座十字架。这便是那农夫的生命和圆满,这感性经验的热流。然而,它也使农夫终于濒临疯狂,因为他已无法逃脱。
因为头顶总有山间辉映的异彩;因为有条神秘的冰河,从粉红的浅滩流向松林的幽暗;因为耳畔始终回响着微弱的冰凌声,还有那喑哑的湍流。
河里的冰凌、天上的雪光,它们和生命的流变与温暖永远相隔,但也因此焕发出光彩。它们在头顶超越了一切生命,超越了血液里一切柔润的热火。所以,人必须活在自我否定的光芒之下。
巴伐利亚高地的人身上有种非凡而简净的美,且男女俱是如此。他们魁伟、清朗、端庄,眼神幽蓝而深邃,瞳孔小而紧缩,虹膜又异常犀利,就好比强光照射着蓝冰。他们四肢匀称、健硕,身体线条挺直、分明,仿佛是用生命的原料雕琢出来的,贞静而又疏离。他们行经之处,一切都会后退,就如同遭遇了清冽、寒凉的空气。
这就是他们的美丽之处,这非凡而简净的孤立,仿佛每个人都想要和别人隔绝,一步步直到永远。
然而,他们却又是欣喜活泼的;这几乎是唯一深契艺术之魂的民族。今天,他们仍在凭借圆融的直觉诠释和演出神秘剧 ,仍在山间的平畴奇怪地放歌,他们酷爱各种幻戏和哑剧,他们的游行和宗教祭礼庄严、隆重又狂热。
这是个极力追求神秘感官愉悦的民族。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源自血液,一颦一笑都别具意涵。
学习凭借的是感性体验,思想则有神话、戏剧和歌舞。总之,样样都离不开血液,事事都与感官相连。这里缺席的唯有智识,因为智识乃是体热的充盈;它并未被割裂,而是被湮没了。
与此同时,头顶上总有那雪光映照出永恒、否定的光芒。下面是勃发的生机,不断有精巧的热血喷涌、倾泻;上面则有非存在放射出不变的光芒。而生命终将逝去,化为这不变的光芒。夏日与大地上绽放的蓝白色花朵终将逝去,连同人的辛劳与狂喜一起凋谢,幻化为头顶盘旋的异彩,幻化为透亮的清寒,等待迎回暂已化为存在的一切。
问题已经露出太多端倪,农夫已经别无选择。命运高悬于头顶,熠熠生辉,永恒而不可思议的非存在。而我们的此生,这辛劳与肉体之温暖经验的合体,始终向着天上不变的光芒,向着那永恒的雪光奔流而去。而这便是那永恒的问题。
无论歌舞、演剧还是身体的爱与狂喜,无论复仇还是虐待,无论劳作、忧伤还是宗教,到*后总是同样的问题,总要归于那璀璨的永恒之否定。这之后,才能成就那高地农夫的完美、圆浑与笃定。他的躯体、他的四肢、他的面庞、他的行止,俱是美的造作,完满圆融。没有变化、希冀或成就,一切尽是今在永在。这问题乃是恒定、永久、不变的。一切的存在与逝去都是这问题的显相,而问题本身却如如不动。是故,也就无所谓“成”,无所谓“灭”,一切尽是今在永在。尔后,才成就了巴伐利亚农民那奇异的美丽、圆满与孤绝。
这一点在十字架上*是显然。木雕的塑身留存了它的根本,脸庞空漠而僵硬,几乎没有表情。于是你才惊觉,这里的男女面容竟都是如此贞定而规训,端庄却又木讷,就像木雕泥塑似的。此外,它还暗含了一种尖刻,秘密而残酷。这都是那大美,那纯粹而变幻之美的一部分。基督的身体亦是僵硬而规训的,但它却匀称而至美,恒定的张力使之成为清朗的一体。全身上下没有动作,也不可能有丝毫动作。其存在终究是恒定的。整个躯体凝定于一种知识,洵美、周全。这是一副扎着铁钉的肉身,但它并未衰竭、僵死。它仍然硬挺,深知它自有无可否定的存在,确信感性经验的绝对真实。他虽然被钉十架,命运已无可挽回,但在那命运里却获得了所有感性经验的力量和欢愉。所以,他专心一意接受了这命运以及神秘的感性愉悦,成全、完满。他的感性体验是超凡的,已经臻于生死交并的殊胜之境。
意大利的黄昏 作者简介
戴赫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英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出生于矿工家庭,当过屠户会计、厂商雇员和小学教师,曾在国内外漂泊十多年,对现实抱批判否定态度。他写过诗,但主要写长篇小说,共有10部,最著名的为《虹》(1915)、《爱恋中的女人》(1921)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1928)。
- >
姑妈的宝刀
姑妈的宝刀
¥11.4¥30.0 - >
中国人在乌苏里边疆区:历史与人类学概述
中国人在乌苏里边疆区:历史与人类学概述
¥24.0¥48.0 - >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20:论自然选择(英汉双语)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20:论自然选择(英汉双语)
¥6.3¥14.0 - >
自卑与超越
自卑与超越
¥13.5¥39.8 - >
唐代进士录
唐代进士录
¥19.1¥39.8 - >
我与地坛
我与地坛
¥16.8¥28.0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有舍有得是人生
¥31.5¥45.0 - >
巴金-再思录
巴金-再思录
¥33.1¥46.0
-
云没有回答
¥23.9¥48 -
哒哒哒哒菜园记
¥14.4¥45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彩虹几度
¥40.8¥48 -
希腊神话:宇宙、诸神与人
¥32.9¥49 -
活着为了相爱
¥15.9¥49.8 -
毛茸茸
¥13.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