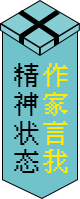-
>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注音版:小妇人(九品)
-
>
中考现代文阅读答题必备公式(备考2023)
-
>
作文指南--怎样描写
-
>
汉语大字典 袖珍本第二版
-
>
寂静的春天(文联平装全译本)
-
>
追随:中国打工子弟心灵笔记(签名本)
-
>
趣味科学丛书--趣味数学思考题
呼啸山庄 版权信息
- ISBN:9787505732889
- 条形码:9787505732889 ; 978-7-5057-3288-9
- 装帧:70g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呼啸山庄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大众读者1.关于“丧”,《呼啸山庄》比《人间失格》早了一百年! 2.关于爱和恨、背叛和复仇的史诗级名作。毛姆心目中的十大小说之一。 3.入选《纽约时报》“世界十大名著”和BBC“100部文学作品”。 4.常年入选中小学阅读书目,英美文学绕不过的英国文学明珠。 5.它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奇书”,曾一度被列为“禁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说:“读过犹如拥有一种财富。” 6.《呼啸山庄》说出了爱情的真谛。我认为它当之无愧是古今中外所有写爱情的小说中极为深刻的一部。——徐志摩 7.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艾米莉·勃朗特和《简爱》作者夏洛蒂·勃朗特、《艾格妮丝·格雷》作者安妮·勃朗特。 8.《呼啸山庄》在面世后的四十多年里一直被冷落,直到十九世纪末,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一部“*好的散文诗”。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唯独《呼啸山庄》没有被时间遮没了光辉。 9.附赠家族图谱,厘清人物线索;收录根据英国学者考证总结的《呼啸山庄》大事记,辅助阅读。 10.我穷尽一生的恨与报复,在爱复活的那一刻,蓦然消逝。 11.爱恨情殇不断流转,终成了我生命中不死的时光。 12.当我忘了你的时候,我也就忘了我自己。 13.比男人更强大,比孩子更单纯,她的性格是与众不同的。——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作者,艾米莉的姐姐)
呼啸山庄 内容简介
《呼啸山庄》是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以爱情和复仇为主题的小说,讲述了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两代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仅凭借这部著作,艾米莉·勃朗特奠定了在世界文学目前的地位。出版于1847年,但在面世后的四十多年里一直被冷落。进入20世纪以后,这部小说便如磁铁般攫住亿万读者的心。可以说,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唯独《呼啸山庄》没有被时间的尘土遮没了光辉。
呼啸山庄 目录
目录
**卷 001
第二卷 181
《呼啸山庄》大事记 395
译后记 399
呼啸山庄 节选
呼啸山庄 **卷 **章 1801年——我拜罢房东刚刚回来——这位离群索居的芳邻往后还够让我麻烦的呢。这一带地方的确是妙不可言!我看整个英格兰再也找不出这么远隔尘嚣的安身之处了。真是厌世者得其所哉的天堂——而希思克利夫先生和我又刚好凑成一对儿,可以共享这一派荒寂。好一个顶呱呱的伙伴!我骑马走上前去就望见他那一对黑眼睛,满腹狐疑地觑在眉毛底下;待我报出自家姓名,他更是决心设防,将那些插在背心里的手指头往里插得更深。在这样一种阵势之下,他很难设想,我对他是心怀何等的热忱。 “你是希思克利夫先生吗?”我问他。 点了一下头就算是回答。 “先生,我是洛克伍德先生,你的新房客。我刚一到达就不揣冒昧立刻前来拜访,是想表明,我一再恳求希望租下画眉田庄,没有给你造成不便。我昨天听说,你原先曾经有些担心——” “画眉田庄归我所有,先生,”他不觉一愣,打断我的话头说,“要是我挡得住,我绝不允许什么人给我造成不便——进来!” “进来”这两个字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表示的是“滚蛋!”的意思。甚至他倚着的那扇门,对这两个字也并未应声启动。我想正是此情此景让我决定接受他的邀请,因为我觉得,一个比我自己还要落落寡合得出奇的人,倒也很有点意思。 他看到我那匹马的前胸都快要蹭到栅栏了,才当真伸手打开链闩,然后阴沉着脸领我走上甬道。我们走进院子的时候,他大声呼叫: “约瑟夫,把洛克伍德先生的马牵过去;再拿点酒来!” “我想这大概就是咱们的全班家仆了吧,”这一声双料的命令使我作如是想,“怪不得石板缝里长了草;牛成了仅有的篱笆修剪工。” 约瑟夫年纪不小了,不对,是个老人,也许还很老,尽管精神矍铄,身体健壮。 “老天爷帮帮俺们吧!”他从我手里把马牵过去的时候,憋着一肚子火气压低嗓门自言自语,一边说还一边朝我脸上扫了一眼,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让我不得不慈悲为怀,设想他必定是需要神力来帮助消化他那顿饭食,所以他那脱口而出的虔心求告和我的不速而至并无瓜葛。 “呼啸山庄”是希思克利夫先生住宅的名字。“呼啸”是当地一个意味深长的形容词,用来描绘在狂风暴雨恣意肆虐的天气,它坐落的处所那种喧嚣噪乱的情景。其实这里想必是一年四季空气明净,清新爽朗。你只要看一看房子尽头那些疏疏落落、干枯低矮极力倒向一边的枞树,还有那朝一边伸着细枝、好像在向阳光求乞的荆棘,就会想见从山那边刮过来的北风的那股劲头了。幸亏建筑师有先见之明,把房子造得结结实实:狭窄的窗户都深深地砌在墙壁里面,房子的四角都有巨大突出的石块护卫着。 迈进门槛之前,我站住观赏了一下房子前脸上大肆装点的那些奇形怪状的雕饰,特别是正门周围的那些。在门楣上方那一大堆碎裂的鹫头飞狮和不知羞臊的小男孩中间,我看出了“1500”这个年份和“哈顿·恩肖”这个姓名。我本想来一点儿评说,再向这位乌云满面的房东打听出点儿这个地方的简史,可是他站在门口的那副姿态,就像是要求我要么赶快进去,要么干脆一走了之,而我可不想尚未登堂入室一窥奥秘,就撩拨得他更加不耐。 一迈步我们就进了这一家的起居室,根本没有什么穿厅或过道:这里他们美其名曰“堂屋”。通常堂屋包括厨房和客厅,不过在呼啸山庄,我看厨房整个给挤到别的地方去了;至少我听出来在尽里边有人咕咕哝哝地说话,还有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的响声;而且在大炉子那边,我看不出什么烤、煮或是烘的迹象,也看不见墙上挂着什么锃光瓦亮的铜煎锅和锡漏勺。屋子的一头,确实倒是映照出了堂堂皇皇的光和热,因为那儿有一口又宽又大的橡木橱,上面摆着一些巨大的白镴盘,中间还夹着银壶、银杯,一排高出一排地一直码到了屋顶。这里的屋顶从没装过顶棚,整个内里结构只要留神尽可一览无余,只有一处地方给放着燕麦饼、一串串牛腿、羊肉和火腿的支架挡住了。壁炉上面挂着各式各样粗制滥造的旧枪和一对马枪,壁架上一溜摆了三个涂得花里胡哨的茶叶桶作为装饰。地面是光滑的白石板。几把椅子都是高背的,结构简陋,漆成绿色。在背亮的那一边,还藏着一两把笨重的黑椅子。橱柜下面的拱洞里卧着一条猪肝色短毛的大母猎狗,四周围着一群汪汪乱叫的小狗崽儿,还有几条狗则在另外一些隐蔽处所蹿进蹿出。 这房子和家具如果是一个普通北方庄稼人的,倒也不算稀罕。这种人常常是生就一副倔强的面容,穿着过膝短裤,扎着绑腿,使两条腿显得又粗又壮。如果你在晚饭后挑好时间去,那么在这一带山区方圆五六英里到处都会看到这种人:坐在圈手椅里,面前的圆桌上放着一大杯冒泡的麦酒。但是希思克利夫先生与他的住所和生活方式却形成一种奇特的反差。从外貌看,他是个黑皮肤的吉卜赛人,从服装和举止看又是位绅士——也就是像许多乡绅一样的绅士:也许颇有点不修边幅,不过还不至于看着使人觉得不大得体,因为他的身材挺拔,相貌端正,而且还带点郁郁寡欢的神气,有人也许会觉得这是他因教养不足而显得自大——我对他则心生一丝同情,觉得并不是那么回事;我凭直觉知道,他矜持的根源出自讨厌矫揉造作地表露感情——讨厌将彼此的情意表露在外。他或爱或恨,同样都是深藏不露,而且他又把为别人所爱所恨,都视作对他的冒犯——不行,我这样离题太远了——我这是把自己的一套想法肆意扣在他的头上。希思克利夫先生遇到可能交上的朋友,会不伸出手来,这和我也会这样做的理由可能完全不同。就让我总想着我的脾气差不多得说是独一无二算了:我亲爱的母亲过去常说,我一辈子也不会有一个舒适温馨的家,而且刚好在今年夏天,我就证明了自己不配有这样的家。 那时候我在海边享受了一个月的好天气,和一个极其迷人的姑娘殷勤为伴,她尚未对我属意的那阵儿,在我眼里真是仙女一般。我言谈中间“从来没有吐露过我的爱情”,可是如果说眉目自能传情,那么*不开窍的傻瓜也能猜想到,我已经神魂颠倒了。她终于懂得了我的心思,而且回送秋水一泓——要多甜美就有多甜美的一泓秋水——可我是怎么办的呢?我羞愧难当地招认——就像一只蜗牛,冷冰冰地缩回来了,每一次秋波一瞬,都让我显得更冷,缩得更远;这一来,这位无辜的小可怜儿对自己的感觉也起了疑心,为自己闹的误会不胜惶惑,竟撺掇着她妈妈溜之乎也。 正是由于这样秉性乖张,我就得了一个故作无情的令名,只有自己心里明白,这有多么冤枉。 我在炉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是正对着我的房东走过去的那一把,为不显得冷场,我想伸手去摸摸那条大母狗,她已经离开了她那窝小崽儿,像狼一样偷偷溜到我的腿后面,撅着嘴巴,露出白牙,流着口水,准备咬我一口。 我的抚摸引得她从嗓子里发出一长串咆哮。 “你*好还是别理这条狗,”希思克利夫先生应和着狗的咆哮,发出一声嗥叫,还把脚在地上一跺,镇住了那条跃跃欲试的狗。“她还不习惯,还没给宠坏——不是当宠物养的。” 然后他大步走向一个边门,又大叫一声: “约瑟夫!” 约瑟夫在地窖深处隐隐约约地咕噜了几声,可是并没有要上来的样子,所以主人就下去找他,留下我一个人和这条凶恶的母狗面面相觑,还有那两条凶险狰狞、浑身粗毛的牧羊犬,他们和母狗一起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严加提防。 我静静地坐着,还不想马上同他们那些獠牙打什么交道——可是我想他们不会懂得沉默也是一种侮辱,便对这三个狗东西挤眉弄眼,做起了鬼脸。这一下可糟了,不知是哪一副面相惹恼了那位女士,竟然让她暴跳如雷,直向我的膝盖猛扑过来。我把她一下扔了回去,又急忙把那张桌子拉过来,挡在我们中间。这一来更激怒了这整个的一窝蜂,六七条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四条腿的恶魔,从藏身之处一下蹿了出来,扑向他们共同的目标。我感到他们专门攻击我的脚后跟和上衣下摆,于是我一方面使出了*大的劲,抡起拨火棍挡开那几条大狗,同时不得不高声叫喊,要这家子来人帮助重建和平。 希思克利夫先生和他那个仆人从通地窖的阶梯爬上来,那慢慢腾腾的样子令人恼火。我觉得他们就像平常一样,没有加快一分一秒,尽管壁炉这边狗群又咬又叫,闹得雷鸣电闪,风狂雨暴。 幸好一个人从厨房里赶出来先解了围。这是一个健壮的妇人,扎着长袍,光着胳臂,红光满面。她把煎锅当武器,抡着冲到我们中间,再加上大喊大叫,这场风暴就像变魔术似的一下子平息了,等到主人来到现场的时候,只剩下了她,胸脯仍然一起一伏地就像狂风过后的大海一般。 “真见鬼啦,怎么回事?”他瞪了我一眼问道。受到了这样的怠慢之后,又看到他这副神气,简直叫人难以忍受。 “真是见鬼啦!”我咕噜起来,“就是那群魔鬼附体的猪也不会像你这些畜生这样凶神恶煞似的,先生。你兴许还会让一位生客跟一群老虎待在一块儿呢!” “不管是谁,只要什么也不去碰,他们是不会找他麻烦的,”他一边说,一边把推开了的那张桌子推回原位,还把一瓶酒摆在我面前,“这些狗保持警惕是尽职尽责。喝杯酒吧?” “不喝,谢谢你。” “没挨咬吧,你?” “我要是挨上了,早给那个咬人的畜生打上戳子了。” 希思克利夫绷着的脸放松了,咧开嘴一笑。 “得啦,得啦,”他说,“你是慌了神儿啦,洛克伍德先生。来吧,喝点酒。这宅子里客人太金贵了,所以我和我养的那几条狗——我愿意坦白地说——都不大懂怎样待客了。祝你健康,先生!” 我鞠了一躬,并且也向他祝酒。这时我也渐渐悟出,为了那一群狗没有规矩就坐着憋气,未免太傻;再说我也不愿意让这个家伙再看着我幸灾乐祸;因为他的情绪往那方面转了。 他大概是出于深谋远虑,觉得得罪一位好房客未免愚蠢,说话也就不再那么简短生硬,删掉代名词和助动词,并且引出他认为我会有兴趣的话题,谈起我目前幽居的那个地方的长处和短处。 我觉得,他在我们触及的这种话题上见解非常精明,而且在告辞回家以前,我已经给鼓动得主动提出明天再次拜访他了。 他显然不希望我再打扰。可我不管怎样还是要去。我觉得,同他一比我居然如此爱好交际,真是不可思议。 第二章 昨天下午雾气重重,天气寒冷。我很想把这段时光消磨在书房的壁炉边,不愿意跋涉穿过石楠草荒地和一片片泥淖到呼啸山庄去。 然而等到吃过正餐(请注意:我是在12点到1点之间吃正餐;这位女管家——同这所房子一起捎带租下来的一位就像主妇一般的太太,不能或者是不愿领会我的要求,给我在5点钟开饭),我怀着这个偷懒的打算上了楼,一进屋就看见一个女仆跪在那儿,身边放着好些刷子和煤桶,正在把一堆堆煤渣压在炉火上,扬得满屋都是讨厌的煤灰。这番景象让我只好立刻转身回来,戴上帽子,步行了四英里,来到希思克利夫的花园门口,这时刚好及时躲过了开头飘下来的鹅毛大雪。 在荒凉的小山包上,泥土结着黑霜变得生硬,寒气砭人肌骨,让我浑身哆嗦。我打不开链闩,就跳了过去,跑过两边是丫杈横生的醋栗树的石板甬道,敲门求进,一直敲到指节疼痛,狗吠大作,也无人回应。 “这一家真可恶!”我心中不禁骂道,“你们这种天生来的刻薄怠慢,让你们活该与人老死不相往来。我起码还不至于大白天也把门锁上吧——我可不管了——我非进去不可!” 我既然下定了决心,就抓住门闩,拼命摇晃。怪头怪脑的约瑟夫从粮仓的圆窗里探出头来。 “你干啥?”他大声叫道,“俺家老爷在羊圈,你要跟他说啥,打粮仓那头绕。” “里边没人来开门吗?”我也对着他大声叫嚷。 “除太太,没人;就由着你骂到夜,她也不会开。” “为什么?你就不能告诉她我是谁吗,嗯,约瑟夫?” “关俺啥事?俺可管不着。”那个脑袋一边咕噜着,一边缩回去了。 雪开始越下越大。我抓住门把手,以图再试。这时一个没穿外衣、扛着干草叉的年轻人从后面场院里走出来。他招呼我跟着他走,穿过洗衣房和一块铺砌过的场地——那里有堆煤的小仓房、抽水机和鸽子棚——*后进入昨天接待我的那间又宽大、又暖和、又舒适的堂屋。 煤块、泥炭和木柴混在一起烧出的熊熊火光,照得人心神愉快;桌子已经摆好,只等端上丰盛的晚餐了,我很高兴看到桌旁那位“太太”,我以前从没想到,他家里还有这么一个人。 我鞠了一躬,站在那儿,心想她总会请我落座。她盯着我,把身子朝椅背上一靠,仍旧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风雪可真厉害,”我说道,“希思克利夫太太,你们家仆人偷懒,恐怕你们家的门也得跟着倒霉;我可是费了好大劲儿才让他们听见我在叫门。” 她就是不开口。我瞪着眼——她也瞪着眼。不管怎么说,反正她是把眼光定在我身上,神情冷淡,漠不关心,叫人格外局促不安。 “坐下,”那小伙子粗声粗气地说,“他马上就会来。” 我从命坐下,清了清嗓子,用朱诺称呼那条恶狗,她在这再次见面之时居然摇晃起尾巴尖,屈尊表示与我相识。 “多漂亮的狗!”我又开腔了,“你有意把那些小狗崽分出去吗,太太?” “他们可不是我的。”这位和气的女主人说。可她说得比希思克利夫本人的答话还要令人反感。 “啊,原来你宠爱的东西在那儿!”我接下去又说,同时把身子转向一个不大显眼的坐垫,上面好像满是猫之类的东西。 “宠爱那些东西才怪呢。”她轻蔑地批了一句。 真够丧气的,原来那是一堆死兔子——我又清了一下嗓子,向壁炉挪近一点,又议论起晚上的大雪。 “你根本就不应该出来。”她边说边起身,从壁炉架上够着两个彩绘的茶叶罐。 她原先坐的地方是背光的,此时我可就清清楚楚看出了她整个的形体容貌。她很苗条,显然未过少女时代:身段优美,那张端庄秀丽的小脸儿,我这辈子还无福一见:娇小玲珑,肤色白皙,发卷淡黄——倒不如说是金黄——松软地披散在她那纤细柔嫩的脖子上,一对明眸要是顾盼含情管保叫你难以招架;不过我这颗多情易感的心总算是福星高照,她这双秀目流露出来的只是介乎藐视一切和有点无可奈何的神色,让人看了只觉得别扭。 那些茶叶罐,她不大够得着,我活动了一下想帮帮她;她却突然转向我,那副神气就像守财奴看到谁想帮着他数他的金币似的。 “我不要你帮忙,”她脱口而出,“我自己能拿得着。” “请你原谅。”我急忙回答。 “是请你来喝茶的吗?”她一边要我回答,一边把围裙系在她整洁的黑长袍上,然后就站在那儿,把一匙子茶叶悬空举在茶壶口上。 “我很愿意喝杯茶。”我回答说。 “是请你来的吗?”她追问了一遍。 “不,”我半带微笑说,“你就是照理该请我的人呀。” 她把茶叶甩了回去,把匙子和所有东西都放回去,然后满脸不高兴地坐回原位。她眉头紧皱,孩子似的撇着下嘴唇,就要哭出来了。 与此同时,那个年轻人已经往自己身上披了一件褴褛不堪的上衣,在炉火前站直身子,居高临下斜着眼看着我,就像我们有尚未清算的不共戴天之仇。我渐渐疑惑起来,他究竟是不是仆人;他穿着粗劣,谈吐鄙俗,毫无能从希思克利夫先生和太太身上看得出来的那股神气劲儿。他那头厚密的棕色鬈发乱七八糟,从未修剪,脸腮上长满乱蓬蓬的胡子,双手像普通做苦活的工人一样变成了棕黑色;不过他的举止还是带点自由自在,甚至高人一等的神气,他对待这家的主妇也丝毫没有露出家庭仆役那种察言观色小心侍奉的样子。 他的地位既然一时难以确认,我想对他那种阴阳怪气的举止还是不理为妙。就这样过了5点钟,希思克利夫走进来,多少将我从不自在的境地解脱出来。 “你看,先生,我说好要来就来了!”我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大声说道,“我恐怕要让这种天气给留上半个钟头了,不知你能不能让我这段时间里在这儿暂避一下。” “半个钟头?”他说着话把衣服上白花花的雪片抖下来,“我奇怪你竟会专门等暴风雪这么紧溜达到这儿来了。你知道,你有陷进沼泽地的危险吗?对这些荒原了如指掌的人,在这种风雪黄昏都常常迷路,而且我可以告诉你,眼下可没有天气好转的指望。” “也许我可以从你那些小伙计当中找一个向导吧,他可以在我田庄那边过夜,明天早晨再回来——你能给我匀出一个来吗?” “不行,我不能。” “啊,真的!那么好吧,我就得凭我自己的那份本事了。” “嗯!” “你是要沏茶吗?”身穿褴褛上衣的那个小伙子一边把那凶狠凝视的目光从我身上转到那位年轻太太身上,一边问道。 “要给他沏点茶吗?”她转向希思克利夫问道。 “快弄好,不是你沏吗?”他这声回答那么粗暴,把我吓了一跳。他说这句话的腔调,显露出一种不折不扣的坏脾气。我再也不想把希思克利夫叫作顶呱呱的伙伴了。 等到准备齐全,他就这样邀请我了—— “好了,先生,把你的椅子往前挪挪。”于是我们所有的人,连同那个粗野的年轻人在内,都挪到桌子周围。大家津津有味地吃喝起来之时,整个屋内鸦雀无声。 我想,如果说这片乌云是由我而起,我就有义务努力把它驱散。他们不可能每天都这样铁青着脸,寡言少语地坐着,而且不管他们脾气能有多坏,他们平常也不至于总是这样愁眉苦脸的。 “真是不可思议,”我一口气喝完一杯茶,正要接过另一杯的当口,开言说道,“真是不可思议,风俗习惯居然能这样养成我们的兴趣爱好和思想见地。许多人就无法想象,像你,希思克利夫先生,这样过着完全遁世隐居的生活,究竟还能有什么幸福可言;然而,我敢说,生活在你这样一个家庭中间,有你那位贤惠的太太,像吉祥仙子似的对你的全家和你的心灵呵护备至……” “我贤惠的太太!”他打断我的话头,脸上露出一副凶神恶煞般的冷笑,“她在哪儿——我那位贤惠的太太?” “我是指希思克利夫太太,你的妻子。” “噢,是呀——嗯!你指的是,尽管她的肉体已经消逝,她的灵魂还在担当守护天使的职务,呵护着呼啸山庄走好运,是这样吗?” 我自觉失言,想尽力弥补。我本应看得出来,双方年龄悬殊,不大可能是一对夫妇。一位是四十岁上下,正是智力强盛的阶段,男人到了这个年纪,很少会异想天开,以为大姑娘会由于爱情而嫁给他;那种梦是留着安慰我们那垂暮之年的。而那另一位则看来还不到十七岁呢。 这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坐在我身边的这个乡巴佬,正端着茶缸喝茶,没洗手就啃面包的,可能就是她丈夫吧;他当然是小希思克利夫了。她这样把自己这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只是因为全然不知世界上还有比他好的人,结果就是将自己活活埋葬!太可惜了——我可得留神,别让她因为我而对自己的婚姻选择懊悔。” *后这个设想看来像是我有些自以为了不起吧;其实不然,我这位邻座简直可以说是令我作呕。而我凭经验知道,我还算是有点魅力的。 “希思克利夫太太是我的儿媳妇。”希思克利夫说。这一下就确证了我的揣测。他一边说,一边转头朝她那个方向很特别地瞅了一眼,充满仇恨的一眼——除非他只是错长了一脸横肉,像其他类似的人那样,从脸上并不能看出他灵魂深处要说的话。 “啊,这就对了——我现在明白了,你真是艳福不浅,拥有这位仁爱为怀的仙女。”我转过身来对我这位邻座说道。 这一下可比刚才更糟了,这位年轻人满脸通红,握紧拳头,分明是一副准备动手打人的架势。不过他好像立刻就恢复了自制,强压着将这通怒火只化作一句冲我而来的伤人恶语,然而我竭力装作没有听见。 “不幸你都没猜中,先生!”我那位房东说,“我们两个人谁都没有特殊的荣幸拥有你说的这位吉祥仙子。她那口子死了。我既然说她是我儿媳妇,那她必该是嫁给了我儿子。” “那么这位年轻人是——” “不是我儿子,管保没错!” 希思克利夫又笑了,似乎是说把他认作那头笨熊之父,这玩笑开得未免过于鲁莽了。 “我叫哈顿·恩肖,”那一位吼叫一声,“我还是劝你,对她放尊重点!” “我并没有表示不尊重。”我回了他一句,觉得他通名报姓时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十分好笑。 他的眼睛死死瞪着我,我也回瞪着他,可是不想瞪得那么长久,因为我怕弄得忍不住要扇他几个耳光,或者笑出声来。我渐渐明确无误地感觉到,我在这样一些舒畅宜人的家庭成员中动辄得咎。这样一种阴沉沉的气氛不仅压倒,而且抵消了我从四周得到的物质享受;我决心谨言慎行,不要再在这个房顶下面第三次冒失了。 吃喝结束的时候,谁也没有讲一句应酬话,我走到窗前去察看天气。 我看到的景象令人堪忧:黑夜提前降临,狂风怒吼,大雪纷飞,天空与山峦变成混沌一片。 “我想没有向导,现在我是回不了家啦,”我不禁惊呼起来,“路都给埋上了吧,而且即使还露在外面,恐怕也是咫尺难辨。” “哈顿,把那十几只羊赶进粮仓的门廊洞去。要是把它们留在羊圈里过夜,就得给它们盖上点什么,再在前面挡块木板。”希思克利夫说。 “我该怎么办呢?”我越来越焦急地接着说。 对我的问题,谁也没有回答;我看看周围,只见约瑟夫给那些狗提了一桶粥来,希思克利夫太太正把身子弯向炉火,拿一把火柴点着玩,那是她刚才把茶叶罐放回原处的时候从壁炉架上碰下来的。 约瑟夫把桶放下来,用找碴儿的眼光把屋子扫了一遍,然后用带着挖苦的口气粗声嘎气地叫喊: “俺真纳闷儿,别人家都出去干活了,你咋觍脸闲待在那儿,真糟透啦!可你是个没用的东西,对你说管啥用——你一辈子也改不了那臭毛病;你就随你娘前头的样儿见鬼去吧!” 一时之间我还以为这一大堆唠叨是冲着我来的;于是我气愤已极,向那个老恶棍跨上一步,打算一脚把他踢到门外。 可是希思克利夫太太的答话却把我拦住了。 ...
呼啸山庄 作者简介
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19世纪英国天才女作家、诗人,世界文坛璀璨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仅凭一部《呼啸山庄》即奠定了她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出身于贫苦的牧师家庭,幼年丧母,曾在寄宿学校接受教育,自幼对文学有着极大的兴趣。1847年《呼啸山庄》出版,但在面世后的四十多年里一直被冷落,直到19世纪末,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一部“最好的散文诗”。进入20世纪以后,这部小说便如磁铁般攫住亿万读者的心。可以说,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唯独《呼啸山庄》没有被时间的尘土遮没了光辉。 艾米莉终生未婚,30岁时因患肺病逝世。英国著名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在诗作《豪渥斯墓园》中艾米莉说:“她心灵中非凡的热情,强烈的情感,忧伤与大胆,是拜伦之后,无人能与之媲美的。”
- >
姑妈的宝刀
姑妈的宝刀
¥11.4¥30.0 - >
新文学天穹两巨星--鲁迅与胡适/红烛学术丛书(红烛学术丛书)
新文学天穹两巨星--鲁迅与胡适/红烛学术丛书(红烛学术丛书)
¥9.9¥23.0 - >
中国历史的瞬间
中国历史的瞬间
¥12.5¥38.0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装共3册
小考拉的故事-套装共3册
¥36.7¥68.0 - >
回忆爱玛侬
回忆爱玛侬
¥12.5¥32.8 - >
推拿
推拿
¥12.2¥32.0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实旅程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实旅程
¥19.3¥35.0 - >
【精装绘本】画给孩子的中国神话
【精装绘本】画给孩子的中国神话
¥17.6¥55.0
-
(2019新)茶馆/老舍
¥15.1¥39.8 -
爱丽丝漫游奇境:英文原版
¥6.7¥20.8 -
中国孩子最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学技术
¥3.5¥10 -
名家名译:基督山伯爵(全2册)
¥13.4¥42 -
美国史上三大总统
¥13.4¥42 -
新语文中下学生阅读指导书目:人类群星闪耀时
¥9.5¥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