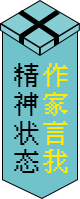-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东京人(全二册)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名人·岁月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伊豆舞女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雪国·琼音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文学自传
-
>
千鹤 碧波千鸟
-
>
古典名著白文本:搜神记
墙 本书特色
以少女之心守望爱情, 以母爱之情幼人之幼。 她的一生, 一代人的命运。 一个女人的爱别离 一位母亲的一辈子 一代人的命运纠葛
墙 内容简介
本书回顾了“我”的养母韩七枝一生的故事。小的时候七枝与江义芳的儿子毛头定了娃娃亲,但毛头八岁时溺水身亡,念情的七枝赶往毛头葬礼现场与他补办了婚礼,嫁入江家。然而,其实七枝早就对毛头的父亲江义芳心有所属而不自知。后来江义芳在江家祖祠祭祀时向七枝表白求婚,二人在一起。好景不长,江义芳去上海办事时竟船只失事,音信全无。她一直没有放弃追寻江义芳的踪影,一生中也遇到不少心仪她的男人,她尝试过想要安定下来,但在历史的洪流中,她遇到的男人都没能陪她走到*后。“我”的生父沈仲景也是心仪她的男人之一,他们二人命运不断纠葛。七枝将沈仲景的三个孩子接受拉扯大,他们却阴差阳错没能在一起。直到*后,沈仲景进了监狱,七枝患上了艾兹海默症患者,把经历一切的记忆都埋藏在了过去。
墙 目录
上部
**章
记忆
第二章
毛头之死
红发卡
一个叫萱的女子
小男人
第三章
家业兴衰
当家的女人
“焦土抗战”
第四章
戏子
沉沦
和悦洲码头
断臂之殇
第五章
抢亲
采花大盗
西垅河
游方僧
枪声
第六章
澜溪街66号
红发卡
“戳妈妈”
大运河
慧公馆
孤男寡女
第七章
盘尼西林
一个国民党士兵
周蕃茄
抓特务
告密者
下部
第八章
泥河小镇
盐场
资本家的儿子
标语墙
杂耍班子
韶云雅居
送子观音
第九章
狼孩
魔道
外星人
祭窑
第十章
永动机
女人与女人
野桃岭
第十一章
道仙洞
美丽的蘑菇
白湖农场
狱医
第十二章
男旦
美人痣
团团
第十三章
知青商场
满坤
失忆症
朝山的和尚
运河上的那条船
第十四章
尾声
墙 节选
记忆 这是我*后一本书了。我在这本书里要说的,是我母亲的故事。 作为母亲*小的儿子,上个月的一天,我度过自己六十六周岁生日。不论是按照联合国划定的年龄界限,还是中国民间的习惯,我都算是一个老人了。一个老人,写一个很老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翁又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我不知道这样的故事是否能吊得起当代读者的胃口。 我曾经有两个母亲,生母和养母。我四岁那一年,我的生母死于癫痫病的发作,因此,对于那个曾给了我生命的女人,我几乎没有任何印象。而在这本书中,凡是我习惯称作母亲的人,那就是我的养母了,她的名字叫韩七枝。 我的父亲沈仲景——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这从他的名字便可知道,我的祖辈对他寄托着怎样的期望。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中医,他对癫痫病曾经有过独到的研究,但他却鬼迷心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弃医从政,他的悲剧似乎也就从那一刻开始。父亲在年轻时的一次荒唐中丢失了一只手臂,从那以后,父亲落得个“拽子”的绰号,但手臂的残疾,一点都没影响他作为一个有魅力的男人所具备的一切品质。他身材高大,有着一头漂亮的头发,即使到了晚年,那一头秀发依然茂密、清澈而又明亮,再配上他高挺的鼻梁,浓密的眉毛,用今天的话说,这样高颜值的男人,自然是很有女人缘的。事实也正如此,他的一生里曾经有过很多女人,但是,没有一个是他真正爱着的女人。直到晚年,他才与母亲结合在一起。而为了这一刻,他几乎耗费了大半生的光阴。据说有一年,他眼看着就要成功了,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将父亲送进了白湖农场——那是一个很大的劳改农场,凡本省上了年纪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个劳改农场的,那里面所关押的,多半是重刑犯人,什么样的罪犯都有——我会在书中写到这个劳改农场的——直到五十六岁这一年他刑满释放,回到澜溪镇。 现在的澜溪镇人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发生在那一年的澜溪粮库集体抢粮事件了,那天晚上,当大批的暴民拿着麻袋或箩筐涌向那座军备粮库的时候,作为这座粮库的负责人,我父亲用他仅存的左臂提了把旧式三八大盖枪拦在了粮库的大门口,就像传说中的独臂将军。父亲明知道那大盖枪里并没有一粒子弹,但他却凛然得像一棵大树,在远方传来的潮水般的呼喊声中,父亲端着那杆枪膛里空空如也的大盖枪大叫着:“不怕死的就过来,我这支枪可不是吃素的啊!”然而,目睹那汹涌而来的不可阻挡的人群,父亲料定他的劫数到了,于是,当人群向他扑来的一刻,他把枪朝空中抛去,枪在空中翻了一个跟斗,而落到父亲手中时,父亲抓起的就是一柄枪托,于是,他就用那枪托朝着自己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来。人们踏着他的身体涌进粮库。事后,澜溪粮库集体抢粮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我父亲也因渎职罪,再加上他令人发指的生活作风问题,数罪并罚,被判了整整十年有期徒刑。那一年,他五十六岁。 是在父亲服刑不久,母亲带着我去了那个广袤无边的劳改农场。在探亲家属登记簿上,母亲用颤抖的手写上自己的名字“韩七枝”,而在“与犯人关系”一栏,母亲写上“夫妻”。这是母亲**次以这样的身份去探望父亲,不用说,这让心如死灰一般刚刚开始他的劳改生活的父亲激动无比。要知道,他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足足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里,父亲向母亲曾发起过一次又一次进攻,然而,却一次又一次在母亲的冷漠面前败下阵来。父亲的出事或许让母亲意识到,父亲几十年的命运,一切的一切,都与她密不可分。母亲的那次白湖农场之行,与其说是对父亲的一次精神抚慰,不如说是一次自我灵魂的救赎。 母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世家,虽然她出生后,家族开始败落,她当然没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但家族的血统,还是让母亲有一种大家闺秀的稳沉和持重。直到晚年,母亲仍耳聪目明,作为街道居委会小组长,她在街道上享受着普遍的敬重。她习惯于人们叫她韩七姑,习惯人们请她去评判邻里纠纷,处理一些棘手的家庭琐事。母亲拒绝儿女们的盛请,一直独自住在镇上那栋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屋子里。那一年冬天,当我们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陆续从各自的谋生地赶回澜溪时,母亲已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三天了。那一次母亲又一次幸运地逃过了死神的追杀,但接下来,母亲像是彻底变了一个人。严重的失忆症让她记不清她曾经做过的一切,甚至认不出我们这些至亲的人。她茫然地看着我,说:“你这个哥哥,你是从哪里来的?”对着我的女儿说:“你这个大姐,你坐啊。” 母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艾兹海默症患者。她已经记不清她在这世上究竟活了多久,她甚至叫不出任何一个晚辈的名字,也弄不清她所有晚辈的相互关系,有时她把兄弟当作父子,把姐妹当作母女,可以说,她的世界一片混沌。母亲整天疑神疑鬼,总觉得所有的人都在企图谋害她,她每天翻箱倒柜,检查她的衣物是否被盗;她开始嗜钱如命,但她却再也分不清十元与一百元之间的区别。她收藏了半口袋硬币,足足有四五斤重,整个漫长的白天和夜晚,母亲都是把这些硬币翻来覆去倒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数着。当然,她总是无法理清她的家当究竟是多少,她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将她的这些钱如愿花掉。她就是这样打发着她的显然多余的晚年时光。 我的母亲韩七枝——从这个名字来看,她该是家中*小的女儿。我的外祖父—— 我当然无从见过他老人家。在我十八岁那一年的夏天,一群人突然闯进了我的家。他们在我家的楼上楼下整整忙碌了一个多小时,直到那群人离去,在一片狼藉的楼道里,我意外地发现一张褪色的老照片。照片上的老人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真正是面目俊朗,风度翩翩。只是,从相貌来看,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母亲韩七枝的影子。 我的外祖父,曾被寄予家族中的厚望而与一群年轻人留学德国,所学的却是毫无用处的逻辑学。因为一次恋爱的经历,老人家受到刺激,从此一蹶不振,人也就渐渐地萎靡了,不得不提前结束他的留学生活,提着一只皮箱,回到那个被称为“江南小上海”的和悦洲二道街上。祖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田产或是房契,晚年的外祖父只能以替人写一些讼文,或者就被江南某家塾馆请去做一名塾师以维持生计。偏偏在我母亲诞下不久,一场偶发的恶作剧丢掉了外祖父的性命。据说那一次外祖父是去洲头一个人家吃酒。从洲头到二道街,需经过一条野路,那所谓野路中的一截,是一片乱坟冈。外祖父的胆子一向大的,他也常去洲头的朋友家打牌或是喝酒,一般说来,外祖父并不在那人家过夜。那天晚上,带着几分醉意的外祖父在微朦的月色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里走去。每走几步,老人家便听到身后沙沙的声响,而等他心生疑惑,驻足谛听时,那奇怪的沙沙声便戛然而止。依照老一代的说法,人在走夜路时,是不可以回头张望的,因为你的祖宗们不灭的阴魂会在你的夜行中暗暗地保护着你。你若是回头,祖宗们便觉得,你是让他回去了。当然,现在的人们是不会相信这些鬼话的。奇怪的是,那天晚上,外祖父走快,那沙沙之声便响得紧密,外祖父走慢,那沙沙之声便也响得轻缓。外祖父终于忍不住回过头来,也是在他一回头间,他终于发现自己正好走在那片乱坟冈上。我实在无法描述当时的情景,当时我听到这个故事时,正是我童年的某一个夏夜,当母亲把她父亲的这段经历当作故事讲给在石板路上乘凉的街坊四邻们听时,恰好我恶作剧的姐姐大喊一声:知柏!当时我正沉浸在母亲的那个恐怖的故事中,姐姐的这一声喊叫,立即让我毛发倒竖,我当即吓得大哭起来。据说外祖父终于回到二道街的家时,他的那件长袍从里到外像是被水浸泡过。一进门,老人家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人事不省。虽然家人很快就发觉恶作剧者束在外祖父发辫上的一把干荷叶,但外祖父在天亮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外祖父一死,让原本并不景气的家庭顿时陷入一片灾难之中。我的母亲韩七枝也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中走进江南江村她的一个表亲江义芳家。这一年,她十二岁。 我在述说着母亲的故事,不知什么时候,母亲醒了。她揉了揉迷糊的眼睛,说:“他有两把枪,一把毛瑟枪,还有一把是勃朗宁,勃朗宁是从一个土匪手里买来的,买回来才晓得是上当了,从来都没打响过……”母亲说着,突然哈哈大笑。 我们早就习惯了母亲突兀的插话,我们希望她能接着这把枪说下去,但她却抹了一把口角的粘诞,摊开手掌,那里有一只老式发卡。 “原来有两只的,被毛头带走一只……”正在上大学的我的内侄说。的确,母亲的故事太老旧了,就像祥林嫂的“我真傻,真的……” 不久前,我读到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我的母亲手记》,这让我突生妄想,带着母亲,沿着母亲从幼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的生活足迹走一遍,或许,能够重拾母亲失去的记
墙 作者简介
黄复彩,1949年生人,籍贯铜陵,现居住安庆市。中国作协会员,著名佛教文化学者,资深媒体人。出版各类著作近二十种。其长篇小说《红兜肚》为中国作协2007年重点扶持作品,获2007-2008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奖文学类一等奖。本书为作者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为安徽省作协第三届长篇小说精品扶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