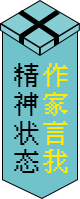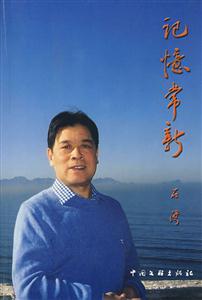-
>
我与父辈(九品)
-
>
商市街 回忆鲁迅先生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彩虹几度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古都·虹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舞姬·再婚者
-
>
碧轩吟稿
-
>
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第三辑)(全十五册)
记忆常新 内容简介
本书包括:红楼故旧;不幸年代的幸运诗篇;难得一聚;守卫记忆;作家与作协会员;说长道短;小书大做;横看排行榜;草台班子;字不离文等散文作品。
记忆常新 目录
红楼故旧
不幸年代的幸运诗篇
难得一聚
黄桥烧饼
杨烈宇伯伯
守卫记忆
偶见梅娘
从政从文两相宜
不辱使命
*早的话剧女明星俞珊
“这个女人很刁”
龙世煇轶事
也说京城名编
远飞的不死鸟
一个古老曲种的新生
一代跤王双德全
擦鞋卡
同在蓝天下
长大以后播种太阳
第二辑
何来“驴在叫”?
作家与作协会员
诗的净土
张学良将军的幽禁诗词
说长道短
小书大做
横看排行榜
有感于杨绛“点烦”
献身文学
“副高”之憾
艺术成本
独苗现象
草台班子
遍地画家
城雕姓“城”
字不离文
小广告背后的大问题
带血的煤和该骂的人
生死攸关
仿写《公仆铭》
第三辑
还鸟以天堂
丹顶鹤放飞
走进朱鹮故里
成语典故之城
又见红旗渠
大自然的乐土
比萨斜塔
“屁”钱
享受阳光
人生公园
丹麦新童话
从桌山到好望角
后记
记忆常新 节选
红楼故旧
去年年末,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一座设计新颖、气势恢弘的中国电影博物馆在京开馆,我有幸在开馆的*初几天,去看了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展览。一部中国电影发展史,像一条星汉璀璨的银河,在观众的面前潺潺流淌,令人目不暇接。蓦然间,一张似曾相识的明星照,跳入我的眼帘,着实令我一惊!细一看照片说明,呀,果然是她——姚向黎!从1950年到1952年,她主演了《民主青年进行曲》、《无形的战线》、《一贯害人道》、《新儿女英雄传》等故事片,出镜率如此之高,这在当时的青年演员中,极为少见。尤其是她在我国首部惊险反特影片《无形的战线》中饰演的崔国芳,是新中国电影史上**个女特务形象,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与我妻子是同事,二十多年前,曾是我家的邻居。那时,我们都住在东单三条56号院。说是小院,其实只是一座家家都挤在楼道里做饭、共用一个水龙头的二层小红楼。自从1986年我搬进中国作家协会的住宅楼后,就再也没见过姚向黎。猛一见到她年轻时代的倩影,不禁使我回想起那座已经消失的小红楼……
记得很清楚,我家是1969年春天住进那座已有上百年历史的法式小红楼的。尽管我们*初住的一间楼下阴面的小房间仅八九个平方米,但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可是寸土寸金之地啊!当时我妻子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小红楼就坐落在东单与王府井的中心位置,她到剧院上班,仅一二百米路,近便之极。*为有利的是,小红楼就在协和医院的西南角上。女儿出生的头天晚上,我正在应约为《北京日报》赶写一篇剧评,因答应第二天上班时就得交稿,妻子的腹痛虽已明显加剧,我还直劝她再忍一忍,等我把文章的*后一段写完。好在协和医院近在咫尺,急就章搁笔,我就让妻子坐到自行车的后坐上,把她送进了协和的产房。拂晓时分,女儿就顺利降生了。也就是说,我女儿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那儿度过的。
那是一段极不平静的岁月。女儿出生才三个月,我就下放去了“五七”干校。有一天早晨,妻子尚未起床,正给女儿喂奶,突然有一男青年破门而入,痴痴地盯着她袒露的胸部不走,她怕他行无礼之举,便惊叫起来。幸好住对门的剧场经理王明仁闻声而至,才为她解了一难。妻子后来告诉我,那闯讲我家的男青年就是姚向黎的二儿子,因高考落榜而受刺激,患了精神病。姚向黎当时住在小红楼的半地下室,日子过得相当艰难,丈夫过世之后,大儿子又因患血癌而亡,小儿子还因在“文革”中失去求学机会而四处游荡,误入歧途……在住进小红楼之前,我从没见过姚向黎,只听说她毕业于延安鲁艺,是个名演员,建国初期她主演的多部影片公映时,我还在江南农村读小学,尚不知电影为何物。加上“文革”剥夺了她再登舞台的权利,我就失去了一睹她展现艺术才华的机缘。只感到她是一个待人谦恭温良的长者,与邻居们和谐相处,总是面带微笑地问寒问暖,叙说家常。邻居们对她的遭遇也都十分同情,多有体谅。因此,每当她二儿子在院子里闯了什么祸,往往都瞒着她,免得她伤心落泪,又得真心实意地挨家去赔不是、道感谢……
我1973年春下放归来,母亲从江南来京帮我们照看女儿,搬进了王经理腾出的一间20平米的房子。未料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波及京城,睡梦中,只听我母亲惊呼:“啊呀!天摇地动啦!”所幸小红楼只是被震掉了东北角的一个房檐,而没有坍塌。但在人人都成惊弓之鸟之日,就谁也不敢在这危楼里住了。我家先是在长安街头住了两个月的防震棚,后又在院部暂住了两三年,等我们再回到已修缮并加固后的那座小红楼时,原先的住户少了好多家,我才搬进老演员姜祖麟腾出的两间房子,结束了祖孙三代长年挤在斗室的困境。我只知姚向黎后来调到中央戏剧学院教表演去了,但不知她在地震之后把家搬到了何处,前些年却突然听到了一个令我毛骨悚然的不幸消息:她那不争气的小儿子,刑满释放后竞逼她交出所有积蓄不成而一怒之下把她杀害,随后他就畏罪自杀……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展出的姚向黎的明星照是那么风姿绰约,光彩照人,谁会想到她生命的结局竟如此血腥和凄惨呢?
参观中国电影博物馆归来,我就从姚向黎说起,向妻子把当年老邻居们的近况打听了一个遍。说也巧,没隔几天,正好老邻居小毕打电话来约我去她家玩牌,而邀来的新牌友,竟是大名鼎鼎的杜高先生。杜高和小毕的丈夫老程不仅建国初期在青艺共事,而且也是同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难兄难弟。杜高得知老程1979年落实政策后回京,搬进东单三条56号院时住的就是我家地震前的那个房间,便饶有兴致地说:“那座小红楼可有故事啦!解放初,那里东西两部楼梯,楼上楼下只住四户人家:金山、孙维世夫妇,石羽夫妇,张正宇夫妇和张逸生夫妇。”我告诉他,当我住进去时,已变成十几户人家,他说的这四对名艺术家中,就剩张逸生夫妇还在,但只留有一间大房了。杜高问:“张逸生成名也很早,你一定知道吧?”我答:“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郭沫若曾尊他为‘一字师’。”
说起“一字师”的由来,那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1942年4月3日晚,郭沫若的名剧《屈原》在重庆柴家巷的国泰剧院首演,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腾的海洋,获得了巨大的轰动效应。郭老很感振奋,天天亲临剧场,不是在台下细心观察观众的反应,就是站在条幕旁和剧中的人物一同欢笑和流泪。4月5日晚,他在后台与张瑞芳说到婵娟斥责宋玉的一句台词:“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郭老说:“在台下听起来,这话总觉得有点不够味儿,似乎可以在‘没有骨气的’下边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正在旁边化妆的演员张逸生插了一句,说:“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了。”郭老一听大受启发,高声呼好。当晚的演出,饰婵娟的张瑞芳就照此改了,果然赢得了预期的效果。后来,郭老特地为此写了《一字之师》的文章,随之传为文坛佳话……由此,杜高先生感慨道:“有关这四对夫妇的文坛佳话可多啦!那座小红楼拆得太可惜了。如果能保留至今,很可以当成中国话剧的一座纪念馆。”
我应和他说:“是啊,前些年我在南京见到曾被打成‘胡风分子’的老诗人化铁,他托我回京后打听一位老导演的下落,我就先找到张逸生家去问的。没想到仅两三个月后,他夫人金淑芝就去世了。”
由张逸生,杜高又和我说到曾在东单三条56号院住过的姜祖麟、常大年、陈永惊、冀淑平等老邻居。我告诉他,这几位都是长寿的老艺术家,且后继有人。常大年是化妆大师,活到九十多岁,他临去世前夕,我还见他骑自行车在街上转悠,一生都活得很自在,是个乐天派。他儿子蓝天如今已是知名的影视演员了。陈永惊、冀淑平夫妇的二女儿小梅是改革开放后**批出国留学的,现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中国现当代文学。前年她回国探亲时,特意约请老邻居们聚会了一次。在我的印象中,当年她是小院里*好学上进的女孩,在“读书无用”的“文革”年代,经常向我借书看,一起侃文学。赴美之后,她一直把精力用在学问的钻研上,直到45岁才结婚生子。她的美国丈夫比她小三岁,是个汉学家,谈起中国的戏剧,也如数家珍,头头是道,仿佛他也从小在东单三条那座小红楼里受过艺术熏陶一样。小梅告诉我,他俩正在合作写一篇题为《青艺对中国话剧的贡献》的论文,此次回国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收集更多的资料,包括向尚健在的张逸生、姜祖麟等老艺术家们请教,因为他们毕竟都已入耄耋之年,再不把活在他们记忆中的珍贵资料挖掘、抢救出来,就太可惜了!
1986年,为建东方广场,东单三条56号院的住户们全部动迁,各奔东西。这些年来,随着旧城的改造,仓促间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名人故居被拆掉了,这实在是一种历史的遗憾。虽说在我如今住的高层商品楼里,也住着不少文化界的知名人物,但家家都安装了防盗的大铁门,除偶然在电梯里会照上一面外,几乎都老死不相往来,再也找不到在东单三条56号院住时芳邻间那种亲如一家的氛围了。因此,尽管那座小红楼已经消失,但从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见到姚向黎当年的明星照后,便就激活了我的许多记忆,令我久久回想……
2006年6月2日
不幸年代的幸运诗篇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也即初学写作时,只要有首小诗见报,被人见了,就难免要挨几句批,扣上一顶所谓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帽子。那年月,谁想要成名成家,仿佛就是犯罪!可是,写作就是有一种魔力,你爱上之后,就休想罢手。我是在高中毕业那年的暑假以石湾为笔名发表处女作的,而我进南京大学读的却是历史系,因此,时有小诗在《新华日报》、《雨花》、《江苏青年报》等报刊上发表,头上就多了一顶“专业思想不巩固”的帽子。虽说几乎每个学期总是迫不得已地在班会上作违心的检讨,可我依然痴迷于写诗,到1964年毕业时,我已经在《萌芽》、《新民晚报》、《光明日报》、《诗刊》等报刊上发表几十首短诗了。恰好那年文化部派人到几个名牌大学挑选戏曲编剧人才,先是中文系推荐了我,历史系主管毕业分配的领导也就顺水推舟,让我如愿以偿地实现了从事专业创作的梦想!
我满怀喜悦地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办完报到手续,就直奔天安门广场!大学毕业前,填写分配志愿表时,在去向栏里,我填写的是“农村文化馆站”。因那时我所敬慕的诗人忆明珠和沙白,都在地、县文化馆工作。我觉得那是一个既贴近生活又有**的报刊图书资料的创作基地,*能出作品、出人才。至于进京搞专业创作,是我这个农家子弟从未敢奢望的事。我曾对同学说,这一辈子要是有机会去一趟北京,那就是*大的幸福了。真的,在那个年代,天安门在外地年轻人的心中,真是遥远而又亲近,神圣而又高峻……
可是,我到北京工作才一个多月,对一切都还充满着新鲜感,就奉命下到吉林通化搞“四清”去了,一期“四清”搞完,又留在当地钢铁厂劳动锻炼……随即就是“文革”爆发,搞所谓斗批改,下放到文化部团泊洼“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当时,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都属于“砸烂”单位,初下放时,我们都以为此生不仅再也搞不了文艺创作,而且,怕是北京都回不去了。可以说,在团泊洼度过的艰苦岁月里,我在心中常常默念的是闻捷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我思念北京》:“我是如此殷切地思念北京,/像白云眷恋着山岫,清泉向往海洋,/游子梦中依偎在慈母的膝下……”
在“五七”干校,我是第三批重新分配工作,回到北京的,那是1973年春天的事了。妻子比我晚回京半年。记得那年国庆节,带着我剐从苏南老家接回的不满四岁的女儿去天安门广场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玩,从早到晚,女儿骑在我的脖子上,我几乎扛了她一整天,也不觉得累,兴致之高,至今仍难以忘怀!就在那天,我萌发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好好写一首诗来歌颂天安门,借此抒发我对北京、对祖国和事业的深情——
笑迎一轮红日,
擎起万里晴空,
一身战斗荣誉,
满怀人间春风。
——天安门!
你昂首挺立,
雄伟庄严,气贯长虹;
你红灯高挂,
灿烂辉煌,光耀九重!
在我们的话语里,
你的名字是如此亲切,
提起你便热血沸腾,心湖奔涌;
在我们的心目中,
你的形象是那么崇高,
远胜过百丈层楼,万仞山峰!
我们仰望你金色的城楼,
就像见到祖国母亲端庄的面容;
我们奔向你宽阔的广场,
就像扑进祖国母亲的怀中……
这是我写的《天安门颂》的**小节,全诗共五小节,二百多行,是我学写诗以来所写的*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1974年初夏写成之后,我就投寄给了《解放军文艺》。大约是8月下旬,我突然接到《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打来的电话:“我是李瑛,你写的《天安门颂》我们已经编好,准备在10月号上用。我给你改了几个字,校样就不送来给你看了,行吧?”……李瑛是我心仪已久的著名诗人之一,一听他报出大名,我激动得手都微微颤抖,连声回答:“谢谢、谢谢!”放下电话,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期《解放军文艺》的样刊,是当时刚到《解放军文艺》当编辑的雷抒雁亲自给我送来的。翻开一看,《天安门颂》竟然发在头条位置上,占了整整三页,还请画家配了题图、书写了标题字。抒雁说:“这一期刊物特辟了庆祝新中国成立25周年专栏,把你的诗排在首页,编辑部是经过认真研究后定下的,领导很重视哩!”我很感动。因为在此之前,我向报刊投稿,往往收到的都是铅印的退稿信,少数稿件被采用了,也从没有编辑署名给我写过信,以至当初我在上海、北京几家报刊上发诗时的责任编辑究竟是谁,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此次能遇上李瑛亲自为我定稿,又结识了与我年龄相仿的抒雁,怎能不倍感兴奋呢!
《天安门颂》发表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很快就制作了配乐诗朗诵节目,朗诵者是中央戏剧学院教台词课的冯明义老师,节目播出后,在听众和读者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直到1977年初我出差去长沙,在省委大院里的一面墙上,仍贴着抄写在几十张朱纸上的《天安门颂》。省军区的一位文化干事告诉我,省委大院警卫连的全体官兵,曾在晚会上集体朗诵过这首诗。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末,刚调到作家出版社的年轻女编辑林金荣惊奇地问我:“你就是写《天安门颂》的石湾吗?我们读初中时就集体朗诵你的诗,不信,我的日记本上还抄着这首长诗呢!”……无疑,《天安门颂》是我的成名作。直到近些年,还有读者一见我面就问:“你原先是军旅作家吧?什么时候转业到地方的?”殊不知十年浩劫中文联、作协系统的文学期刊全都被迫停刊了,唯有《解放军文艺》还坚持出刊,团结和培养了一批青年作家,我成了那不幸年代的幸运作者之一。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天安门颂》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所夹着的某些标语口号式的句子,毫无诗意不说,还带有一种明显的“阶级斗争”的色彩。这自然是不足取的。但自《天安门颂、》发表之后,向我约稿的编辑纷至沓来,我在一发而不可收的情形之下,也就积重难返。因此,上世纪70年代末,同在一个创作组的汪曾祺先生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如果你还继续写诗,就得变法!”我在短时内“变法”不成,进入80年代,就索性不再写诗,而学写起报告文学和散文来了。
2005年8月28日
……
……
- >
名家带你读鲁迅:故事新编
名家带你读鲁迅:故事新编
¥13.0¥26.0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有舍有得是人生
¥19.4¥45.0 - >
【精装绘本】画给孩子的中国神话
【精装绘本】画给孩子的中国神话
¥17.6¥55.0 - >
龙榆生:词曲概论/大家小书
龙榆生:词曲概论/大家小书
¥9.1¥24.0 - >
推拿
推拿
¥12.2¥32.0 - >
朝闻道
朝闻道
¥9.0¥23.8 - >
经典常谈
经典常谈
¥22.7¥39.8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装共3册
小考拉的故事-套装共3册
¥36.7¥68.0
-
到山中去
¥17.7¥30 -
我的心曾悲伤七次
¥12.8¥25 -
茶,汤和好天气
¥13.9¥28 -
极品美学
¥18.6¥58 -
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的梦想
¥15.3¥30 -
心安是归处:琦君创作60周年美文精选
¥15.9¥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