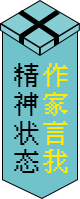-
>
我与父辈(九品)
-
>
商市街 回忆鲁迅先生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彩虹几度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古都·虹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舞姬·再婚者
-
>
碧轩吟稿
-
>
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第三辑)(全十五册)
新书--寄声浮云(精装) 版权信息
- ISBN:9787545819137
- 条形码:9787545819137 ; 978-7-5458-1913-7
- 装帧: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新书--寄声浮云(精装)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喜欢随笔、散文、回忆录,对时代记忆有兴趣、喜欢温暖平凡生活中的人生哲理和生活感悟的读者。既有时代印记,让人顿生亲切,又有世间百态,天空海阔,还有人生经历,生活百味。一篇篇值得细品的精致小文,让人读来有会心一笑之感。温暖的午后,一杯香茗,一片阳光,一本书,获得满满的能量,从别人的故事里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人生。
新书--寄声浮云(精装) 内容简介
《寄声浮云》是一本阅读性很强的随笔集,内容主题以上海记忆、童年时光、游历日记、生活感悟为主。写作风格贴近生活,文字优美,充满生活的美好感悟。类目下既有时代印记,让人顿生亲切,又有世间百态,天空海阔,还有人生经历,生活百味。一篇篇值得细品的精致小文,让人读来有会心一笑之感。温暖的午后,一杯香茗,一片阳光,一本书,获得满满的能量,从别人的故事里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人生。
新书--寄声浮云(精装) 目录
001 逝去的那些生日
010 棚户区记事
052 人生的“偶然”
058 武康大楼记事
075 我那远去的诗缘
087 都柏林拼图
094 我的俄乡纪行
120 京西的鳞爪
131 里斯本杂拌
138 前南散记
167 陕北日记
193 绍兴的烟云
202 苏单印象
224 暮色苍茫鼓浪屿
230 挹浪日本海
239 几番勾留是香江
275 吾家有儿初生时
296 百无所好乐伴书
新书--寄声浮云(精装) 节选
棚户区记事 我人生*初的22年,生活在上海西区一片棚户区 的简屋里,直到大学毕业后报到上班的第五天才搬走。 这“棚户区”的叫法,我总感觉有些暧昧,若在别国, 可能径直就称“贫民区”了。不过,我们的棚户区房 子,也确实不都是席棚毛毡或者铁皮什么的搭成的,有 些也是砖瓦木石正儿八经地盖起来的,若留存到今天, 也许还有点历史风貌的价值呢。 如今的上海,随着这几年大拆大建,连片的棚户区 差不多绝迹了。我住过的那片,坐落在兴国路和武康路 的交会处,周围都是洋房,还多带着小花园,南面更是 有一座伟岸的武康大楼(现在简直是上海地标了),它 的巨大阴影就笼罩在我们那片的粼粼屋瓦上面。怎么说 呢?如果周围的各式洋房是一片茂盛的花草,我们那片 棚户简屋就是掺杂其中的斑斑苔藓。我孩提时代的许多 记忆,关于人和事的,就在这片苔藓中生成。 (一) 说起记忆中的人,我首先想到的常常是老陶。老陶 没什么光荣的,是个挂牌的“四类分子”。这个专有名 词,现在年轻人是不大知道的,而在那个年代,却是 “含菌量” 很高的。从字面上说, 就是四类人: 地 (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总之是阶级 敌人,不久加了个“右”(右派),阵容更加齐整,队伍 愈发扩大了。 我对老陶的身世一无所知,后来听一位跟老陶住得 很近的发小讲,他是个逃亡地主。原来是个没当成还乡 团的人!即便如此,老陶总是个阶级敌人,在人民当家 做主的年代,就要为自己的过去偿还代价,顺理成章归 入“四类”,成了贱民。 那时候,一旦当上了贱民,就有幸从事*光荣的事 业———劳动,而且是*为原生态的劳动,扫地、搬运、 清厕之类,不知道这该算是一种惩罚还是奖赏。总之, 老陶被勒令黎明即起,每天在劳动人民大多还在睡梦中 时,就开始洒扫庭院,这庭院也就是弄堂。早起的鸟儿 先得食,我想老陶的早起,也会有所获吧,比如那份清 静,可他的扫帚一挥起来,无论多么小心,那份清静总 是被搅破了,于是,我的残梦里,也就植入了那抹不去 的“沙、沙、沙”的有节奏的轻音,被撩拨得欲睡不能 欲起不愿。 老陶劳动时,很淡定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 旧中山装,戴着一付旧布袖套(那才是劳动者的标配), 蹬着一双旧解放鞋,双眼也跟着竹枝大扫帚在地上扫来 扫去,因此跟左右穿行而过的人———多半是以各种姿态 匆匆来弄内那座远近唯一的公厕方便的———没有任何交 集。谁顾得上他,他又顾得上谁啊!老陶的头发花白 了,在晨风里微微有些颤动。他的手不像是养尊处优的 地主的手,也许是多年的监督劳动,让他的掌、他的指 先脱胎换骨了,显得很粗糙,好像还有冻疮的痕迹。这 些印象,是我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跳下床,匆匆奔 到对面公厕减轻负担时,在不多的几瞥中刻下的。 老陶的洒扫庭院,或许真的算是有些温柔甚至有些 诗意的惩罚,跟他对人民犯下的罪肯定是不相匹配的。 因此,老陶也别想就如此舒舒服服地等着时光来解放 他,总要为革命再做出点牺牲。20世纪70年代中,上 海流行搞“向阳院”,那是现在如火如荼的社区建设的 前身吧。破陋的弄堂里搞了些环境整治,东刷刷、西弄 弄,甚至还配发了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可是稀罕 物,装在带长脚的木头箱子里锁着,晚上由专人负责搬 到空地上,打开调到五频道或者八频道,放节目给拖着 板凳涌来的各色人等观看。我们那片街区大概把“向阳 院”搞得不错,突然被上级看中,要来开现场会。这 样,就有一番忙乎!“向阳院”建设不能只展示些看得 见、摸得着的玩意,也得演出些看不见却感得到的东 西,比如阶级斗争时刻没有放松。于是,组织了一场批 斗会,作为附近唯一活的监督劳动分子, 老陶荣幸 出场。 老陶在我家门前那棵老桑树下,垂手站立,垂头看 地,一帮半大孩子围着,指手画脚,嚷嚷纷纷。说了半 天,老陶也就一条罪状:不老实。不老实也就一条罪 证:星期天到别的地方去不报告。说重了就是不服群众 管教监督,也许想着变天!老陶本来有些木讷,又自知 理亏,千夫所指之下,想要辩解,嘴里却磕磕绊绊、话 不成句,脸憋红了,头不敢抬,更显出阶级敌人的本色 了。我挤在人群里看着,正有点大快人心之感! 没几年,史无前例的时代结束了。不管老陶有没有 想过,变天是终于等来了。也不知有没有哪家单位为他 举行过隆重的宣布平反的仪式,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平 反,就是“摘帽”而已。但老陶肯定不用再黎明即起洒 扫庭院了,那份劳作,物归原主,由劳动人民自己负责 了。我的睡梦并没有因老陶的停帚而延长,因为我参加 了学校的篮球队,也黎明即起,到学校训练去了。 老陶的家在如今很著名的武康路边上,隔条马路就 是宏伟的武康大楼,那时它颇有些沉闷,常有些人——— 受迫害的政治贱民、挨病痛的社会难民———把它当跳 台,在飞翔中跟大地来个激烈的拥抱。老陶家的房子不 错,是那种老的砖木结构的,当街有连扇的窗户,门上 也有大玻璃,就是阳光被武康大楼挡住了,门前屋里四 季都照不到,*多摊到点已经暗淡的斜阳。老陶个头 矮,虽然不瘦,因为那个身份,人总有些猥琐,但他的 太太模样超过许多婆婆,依然细皮嫩肉,比较丰满,连 带他们那位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女儿也一副小家碧玉的样 子。路过老陶家,总能透过那些明净的门窗,见到母女 两个坐在前厅的床沿,一人一个绣棚,舞动着手。老陶 跌落劳尘时,她们是这样;老陶摘了帽了,她们还是这 样。也常见老陶捧着一个玻璃瓶化身的杯子,坐在靠窗 的椅子上,一边不时地啜着热茶,一边静静地看着母女 两个飞针走线,脸上读不出一丝欣慰的表情。 (二) 有一个人,像老陶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因为他一脸络腮胡须、一身破中山装、一付落拓(也许 该说“落魄”)模样;因为他一付浑厚好嗓、一贯破口 骂街、一人孤苦伶仃。 知道他叫李梦熊———这名字我们小时候也不觉得有 什么特别,还常常把他叫成“李狗熊”,知道他是个神 经病,也知道他原来是音乐学院的。其他的,就不晓 得了。 若干年后,忽然听说陈丹青在书中讲到他,更吃惊 的,是陈丹青的老师、如今大名鼎鼎的木心先生提起 他。木心晚年回忆这位当年的朋友,称之为“旷世奇 才”。我仔细在记忆深处搜索李梦熊的碎片,丝毫不能 验证木心的评价。 李梦熊其实不属于棚户区的,他住在一墙之隔的武 康路400弄一幢三层别墅楼里。他留给我*深的印象, 就是日常在那幢楼的一个小阳台上,对着我们那片烂房 子,居高临下地骂街,一骂往往几十分钟,翻来覆去 的。我的家距离那个阳台直线距离*多二十米,能清晰 地看到李梦熊骂街时口沫四溅、表情激愤的嘴脸,和小 半个身子。听着他仿佛练声吊嗓般的开骂,觉得有意思,出来看热闹,又担心那双冒火的眼睛直视过来,怪 吓人的,所以很有一番忐忑,不敢多暴露。 李梦熊骂的不是家长里短,骂的是国民党,更具体 地说,是骂国民党的帮凶。他用浑厚的低音深沉地吼 道:“湖南街道、湖南派出所,是国民党的看家狗!”这 是他反复*多的一句,也不知跟国民党有什么仇,或者 只是用着当时的话语体系为骂而骂。他跟湖南街道、湖 南派出所看来是有点仇的,至于到底是什么仇,不得 而知。 人们都知道李梦熊骂街是一种日常消遣,一个神经 病,谁会去理他?再说他也没骂伟大领袖和伟大的党! 可偏偏就有捣蛋的孩子要去惹李梦熊,等着看他怒火冲 天、气急败坏的样子。他们会聚到李梦熊住处的窗下, 抬头齐声猛喊:“李狗熊!”等到他一边骂着一边跳到小 阳台上看个究竟时,那帮熊孩子早已溜之大吉。李梦熊 憋红了脸,骂累了,歇一阵,消失了。 不骂街的时候,李梦熊也没什么不正常。那一身深 灰色的中山装,上下都打着补丁,搞得深浅不一、层次 蛮多的样子。这也不算什么,那个年代没几个穿得光鲜 的,李梦熊这一身,看着仍不失齐整,只是裤子明显 短,像是现在女人的九分裤,遮不住脚踝;配的鞋差 点,是磨出破绽的胶底解放鞋,完全是贩夫走卒的标配 了。不过,一副厚厚的玻璃眼镜(后来听说,那是用两 片水晶磨成的),又让他明显像个学究。 关于李梦熊的个人生活,我们只知道他始终孤身一 人,五十来岁头发花白了也还那样。既然是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他也就很是随遇而安了。早上,他常到兴国 路口一个只做早市的饮食摊点,从我那位发小的母亲手 里,买一个大大的夹根油条的粢饭团,据说回家后一掰 二,作早午两顿吃的。傍晚,常见胡子拉碴的他,撑着 那一身落魄打扮,提俩竹壳旧热水瓶,步子迈得很大, 器宇轩昂的样子,抄近道从我住的弄堂、也从我家门口 穿过,到兴国路上的老虎灶去泡一分钱一壶的开水。在 等着水烧开的时候,李梦熊在腾腾水汽中跟老板甜不甜 咸不咸地聊几句,也会逗逗走进来的小孩子,脸上露出 笑眯眯的神情。 除了上面这些事,李梦熊对于我就是一个谜(但我 不知道那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还是在陈丹青听到的 木心先生的回忆里,才知道一鳞半爪。再后来,又看到 网上有回忆文章,李梦熊还真的曾经是声名显赫的人 物:出生云南白族大家,父亲是民国少将、追赠中将 的,表兄是艾思奇;本人是男低音歌唱家,少年时据说 还在重庆给邓颖超当过小交通,40年代末开始参加许 多重要的演出,同台者有周小燕等,培养过杨洪基等一 批声乐人才。通多国语言,晓多国文化,知其者谓之 “卓尔不群,常有惊世骇俗之见”。1958年,李梦熊到 兰州的音乐院校执教,五年后回到上海,就没有了正儿 八经的工作,大概没有哪家单位受得了这样一个狂傲不 羁的人。他一度靠着售卖收藏的古董度日,常放浪形 骸、一醉方休。再后来,就是史无前例的风暴来了,本 来就怪脾气的李梦熊, 就疯了(为什么疯,还是不 知道)。 木心对于这位老朋友的回忆披露后,李梦熊的足迹 被更多地发掘出来。说到他的后半生,自然令人唏嘘, 尤其是他的那段我也曾旁观过的生活,简直可以说是凄 凉。看到网上的文章说,李梦熊住进武康路400弄的房 子,还是一位老房东见他可怜才租给他的,只是个几平 方米大的亭子间,没有地方支床,就打地铺,上有一领 竹席、一床褥子和一条被子,没有地方架桌,就用砖头 垒个小台,放那吃饭喝水的茶缸。千金散去不复来的李 梦熊,靠每月12元生活费糊口,靠居委会低价卖与一 些清仓衣物裹身。他的亭子间老挂着一个装满汽油的瓶 子,说是“随时准备自焚”用的。而在那个家徒四壁的 局促空间里,却有一摞外文书(我想,那应该是风暴以 后的事了吧),1997年他的亲属去上海看他,见他在读 法文版的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后来知道的这一切,都完全出乎我的想象。我甚至 一直怀疑,我少年时代记忆里的“邋耷胡子”(“络腮胡 子”的上海话表达。我们那时候都用这个绰号称呼他), 是否就是这个如今被许多人追捧的李梦熊。一想到就在 这么近的距离上,曾经有一位这样的神秘大才,我总感 到莫名的荣幸。可惜那时太小太无知,完全没有可能去 接触他,更谈不上接近他的真实世界。 那天我去武康路附近办事,完了,不由自主地走进 了400弄。那里的老别墅房子几十年了都没变,不过粉 刷一新了。李梦熊骂天骂地的那个小阳台还在。我抬头 看着那个空空如也的地方,想着往事如沙上的痕迹,被 无情风雨带走了。 我想象着那一弯络腮胡,由凝重的灰黑变成了苍凉 的灰白;那本该在舞台上放歌的天籁之声,变成了天地 间无望的呐喊。 (三) 我住的那条弄堂,贯穿那片棚户区,呈曲尺形,一 头连着兴国路,一头通向武康路,长近百米,两边拉拉 杂杂排列着三十来户人家;加上几条岔弄和两路沿街地 区,总也有六七十户、几百人局促在那里。既然是个小 社会,各色人等就不少,事情也就庞杂琐碎得很。 比方说,作为旧社会的遗存,我们那里至少有三个 家庭是有过大小老婆的。两家后来拆分了,小老婆出门 另过,但还邻近住着。有一家的大妻小妾,居然还在一 个屋檐下。那小妾也已是五十来岁的婆婆了,倒像个童 养媳或佣人一样,整天打理家务。常见她颤巍巍地提着 铅桶,走过长长的弄堂,到马路对面的供水站去提水。 还听大人们嘀咕,你看谁谁谁长得像隔壁的谁谁谁?他 其实就是谁谁谁的儿子。有点乱! 这也难怪,我们脚下的那片地,据说*早是老福开 森路旁的一块墓地。如果搁在当下,肯定改建成街边花 园,供周围洋房居民休闲散步了(如今那里早已拆建成 几栋小高层住宅楼,底楼沿街确实开出了几家咖啡馆, 不仅吸引洋房居民,更吸引洋人居民前来一泡)。可后 来,有些南腔北调的贩夫走卒来这里安营扎寨,搭搭弄 弄,把它变成了一个住活人的街区。既然多是下等公 民,彼此的关系就很有些复杂。我父亲1948年底从老 家江苏连云港辗转来上海,因为有个表姐住在那里,也 前来投奔,混居其中了。 我家边上有棵桑树,树下就是批斗“四类分子”老 陶时的会场。那棵树四五米高,小碗口粗,瑟缩在弄堂 天地里,算不上枝繁叶茂。树上结的桑椹我尝过,水灵 灵、紫盈盈、甜滋滋的,比那时的葡萄、枣子好吃多 了。树上长的桑叶,自然是我们养蚕宝宝时唾手可得的 喂料。 这棵桑树是我家对门的老李种下的,想采桑叶就要 得到他家人的首肯。因为是远近唯一的一棵,来采叶子 的特别多,老李一家不胜其烦,就常常对人家打回票。 有一个启东老头,住在武康路老陶隔壁的,矮矮胖 胖,长着一对鱼泡眼,秋冬经常一顶绒线帽罩顶、一件 棉马甲护身。他的孙子、也是我的发小、我姐姐的同 学,在纸盒子里养着一拨蚕宝宝。眼见着蚕宝宝嗷嗷待 哺,小孩陷入无米之炊,老头心里难免着急,就想在月 黑风高的时候,智取那些桑叶了。 某日黎明前*黑暗的时刻,启东老头出动了。我 想,他一定是偷偷进到我们弄内,来到桑树跟前,瞅瞅 周围没人,连边上24小时繁忙的公厕也静悄悄的,就 手脚并举上了树,应该是很快够到了一人多高位置的那 些宝贵桑叶了。 智者千虑,尚有一失,启东老头并非智叟,想悄悄 来悄悄去,不留下一点动静,是很难的。老李的那位小 脚老母亲,凌晨时照例只能浅睡,所以特别机警,在万 籁俱寂中听到门外有声响,就披衣起来看个究竟。恍惚 之间,老太太看见了树上贴着个黑影,那不是小偷是 谁!于是,顺手拿过门口的扫帚,碎着步子冲上前去, 不管三七二十一,抡起帚柄就向半空里猛挥。 启东老头不上不下地攀在树上,屁股上着了鼓点似 的棒打,躲不开,挡不了。忍了一会儿,只好讨饶道: “奥(别)打嘞,奥打嘞,再打要坏忒嘞!”他*后怎么 下树的,有没有带走几片桑叶,我也没打听全。 话说回来,既然那棵桑树权属老李家,偷采总是 “违法”的,小脚老太拿着扫帚柄,狠打爱孙心切的老 头的屁股,完全是捍卫自家权利的正义之举。 如果是老李,大概不会那么决绝地对待一个总算是 街坊邻居的人。老李喜欢忙另一件事:捡煤球。他常在 蒙蒙亮的晨光里起来,端个板凳,拿把火钳,带个破脸 盆,踱出弄堂,到马路对面饮食店门外,在那一大堆刚 从炉膛里掏出的煤灰旁坐下,火钳开始在煤灰里扒来扒 去,将一个个仍星星点点带火的未燃尽煤球,扒拉到脚 下。火钳头上两片小小的舌头,又忙碌地削去外面的 灰,只留下黑黑的煤芯———老李把它们一一夹进破脸 盆,凑成小半盆了,才慢慢伸腰起身,颇有收获感地收 拾回家了。这时候, 个把小时过去了, 天光已经大 亮了。 老李在邮电局工作,当时,那可是个令人羡慕的职 业,收入也不错。老李的老婆也是从纺织厂退休的,家 里虽然养着老母亲和两个读书的孩子,但生活绝对过得 去,否则,老李也不会有闲心,自制鸟笼养个雀儿玩 玩。可老李就有这么个“嗜好”!虽然在那个年代这不 算什么丢人的,但像我老爸,对老李捡这个便宜,就很 有些不屑。 我是很为我老爸的心灵手巧自豪的,老爸在酒精厂 当锅炉工长,简直是半个工程师,锅炉一般的毛病都找 他修。另外,木工活、电工活、泥水匠的活,他都拿得 起来,办个宴席,无论婚丧,也撑得住。在需要“自给 自足”的时代,老爸绝对是个生活能手。但看到老李用 普通的竹子制作精美的鸟笼,亮一亮工匠手艺,我就不 由地把老爸看低一点了。 只见老李戴上老花镜,坐在小板凳上,屈起的膝头 垫块厚布,用一把普通的宽刃小刀,就能精准地在竹片 上剖出一根根细竹条,再用刀刃卡住竹条,反复划拉, 就做成了一根根规格一致、剖面圆滑的竹丝。把这些竹 丝一一穿进几个钻了一排小洞的竹箍,顶端用一个钮收 口,一个鸟笼的样子就出来了。接着就是安上下开的 “门”、金属的挂钩等等。老李做这一切,不急不慢,不 声不响,不像我老爸有时出个岔,一着急要恨恨地骂个 娘。老李的效率也挺高的,才见他开始剖竹条,可两三 个半天过后,鸟笼就漆上清漆,挂在他家的檐下吹着 风了。 老李家的房子,两层砖木小楼,在那一片破旧简屋 里算齐整的,有一回还当了一次电影外景地,梁波罗在 那里拍过几个镜头。是什么戏,忘了,我也没看过。那 一次,弄堂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我母亲跟我回忆说, 当时还到我们家借过些东西,就是日常使用的竹篮之 类,当道具。前几个月我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见到梁波 罗,说起他曾在我们邻居家拍过戏,梁老师也想不起 来了。 老李安徽人,“肥东”还是“肥西”,没搞明白,反 正口音里是“鸡” “猪”不分的。他比我父亲大几岁, 也是上世纪20年代生人。偶尔他们也一起谈谈钓鱼, 甚至结伴起个大早,跑大老远到郊区去野钓。但总的来 说,两人交集不多,不像我家隔壁的老陈,和我父亲也 是钓友,平时聊得多一点,毕竟他们是苏北大同乡——— 老陈扬州人。老陈的一辆老坦克(像电影《小兵张嘎》 里侦察员老罗骑的那种,带U 型撑脚架的自行车)还 卖给了我父亲,不过价格不便宜。 老陈比老李和我父亲都大几岁,面阔鼻隆,口方耳 大,一脸福相。不过,老陈有严重的肺病,背有点驼, 连带本来也魁梧的身子,显不出高大的形象来。老陈烟 抽得厉害,咳嗽多,痰和鼻涕多,两眼似乎也被熏黄 了,浑浊。他常常一烟在手,就用拇指下厚厚的肉掌部 分,抵住鼻子瞅准墙角擤鼻涕,同时“噗”一声吐出一 口浓痰。我们都怕带病菌,连忙小心地躲开。 老陈是个点心师,还是永嘉路口一家饮食店的“头 牌”。现在上海街头被热捧的老式葱油饼,我*早就是 从老陈那里吃到的,确实,现在买来吃的,样子跟老陈 当年做的一样,但味道绝对超不过老陈的平常之作。老 陈这个“肺痨”,居然堂而皇之在饮食店干了二十来年, 后来还自摆摊头,亲手揉搓出多少进得人口的糕饼,想 来有点后怕!
新书--寄声浮云(精装) 作者简介
王伟,男,1963年5月出生,汉族,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1985年7月参加工作,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伟在1990年代中期就职于《文汇报》,任要闻部副主任;1996年10月,王伟调上海市委宣传部,任新闻出版处副处长;1999年1月,调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任新闻处(后改称新闻发布处)处长;2004年4月,调香港《大公报》,任副总编辑兼大公网总编辑;2013年4月,调上海《解放日报》,出任上海报业集团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