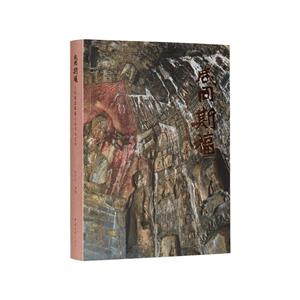-
>
海上画坛
-
>
(精)永恒的巴黎圣母院: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诞生(八品)
-
>
精品画册:海上藏宝录(1函9册)(书盒坏)
-
>
(精)草书字典
-
>
千里江山越千年(中国山水画艺术与千里江山图珍藏版)(精)
-
>
(精)敦煌日历2023
-
>
西洋镜:中国宝塔II(全二册)
咸同斯福 版权信息
- ISBN:9787519051501
- 条形码:9787519051501 ; 978-7-5190-5150-1
- 装帧: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咸同斯福 本书特色
观赏造像记书法的新范本、新视角与新方法 楚默 赵际芳主编的《咸同斯福——古阳洞造像题记及书法艺术》是一本别出心裁、极富创新观念的书法作品集,它收录了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造像题记300余幅。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早开凿的洞,收录了早的造像题记书法。著名的“龙门廿品”中十九品出自古阳洞,历来被视为魏碑的范本。“龙门廿品”被康有为列为必购之碑,集中体现了魏碑的精华;在本书之前,拓本不知印了多少版本。那么,赵际芳所编的这本《咸同斯福》是不是炒炒冷饭,重印一遍“龙门十九品”呢?显然不是。赵际芳曾是一名资深编辑,在《中国书法》杂志社工作十多年,阅过无数写经墨迹,也阅过无数魏碑真迹。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观念、视角全新的造像记书法作品集。该书之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将造像题记书法放在多维文化视野中呈现,并不是单一的题记书法拓片的再版 这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将造像题记作品放在一个具体的佛教文化、制度文化的背景中呈现。题记书法只是一端,更多的篇幅放在该造像题记的文化背景展示。一篇造像题记在古阳洞的什么位置,刻在佛像的什么地方,大小,佛像周围的各种图式、花纹,是弥勒像还是释迦牟尼像,胁侍菩萨什么状貌,胖瘦、姿态、手势、服饰纹路,等等,都有具体交待。也就是说,凡与题记书法相关的整个文化环境,能具体呈现的一律立体式加以陈列。古阳洞高大壮观,一则题记所占的空间其实很小,故将题记放在一个形象生动的佛教文化环境中,题记书法的佛教文化底蕴就得到生动展示,这无疑是一种题记书法展示的新方式。故是一种观念崭新的书法范本。 古阳洞中的佛教造像主要是释迦与弥勒像,因为北朝时流行的佛教信仰主要是信从弥勒佛和释迦佛。《牛橛造像记》称“造弥勒像记”,《郑长猷造像记》谓“为亡父等造弥勒像”;《元详造像记》造的都是弥勒佛像,《元燮造像记》造的都是释迦像,但仍有“二菩萨”。从题记看,发愿人要表达的也是弥勒经的思想。《牛橛造像记》《侯太妃造像记》表达的都是今世不旺、祈求来世昌盛的心愿。弥勒信仰尤适合下层民众,因为经文不长,容易背诵,修行方法简单。古阳洞中也有少量的观音像,那是以后才刻的。如《王仲和造观音像记》(公元521年)、《安定王为女夫闾散骑造观世音像记》,肯定是稍后刻的。 弥勒造像的刀法、造型也都不同于云冈石窟造像。云冈造像较多地反映出犍陀罗及印度艺术的特征,造像雄伟、体胖硕大,衣纹和装饰采用阴刻,是北魏早期的审美观。而到了龙门时代,弥勒和二胁侍菩萨面容清瘦,颈部细长,双肩消瘦,身体修长,形态清俊秀逸。这种崭新的造像风格也体现在《杨大眼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元详造像记》等造像中,显示出龙门造像的新形象,这都有赖于刀法的改进。 所以,观赏造像书法中的佛教文化底蕴,观看题记上方、左右的诸佛像,并不是多余的举措。《咸同斯福》正文篇有一篇赵际芳与胡鹏的重要论文《从北魏制度的建立看古阳洞造像题记》。这篇论文提及“制度”,包括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僧官制度等。不理解这些制度的来龙去脉,也就很难解开造像题记书法的许多谜团。文中举例说:《孙秋生造像记》后增人名都以“唯那”开头,为僧官“维那”;古阳洞中地方官员、僧人造像题记的多少,都与一定的僧官制度、文化制度相关;不同地位的官员,不同技术的工匠都于造像题记书法字体、笔法、刀法有着明显的差异,可见镌刻受各种制度的制约是明显的。 平心而论,过去学习“龙门廿品”书法的人很少知道题记书法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也不知造像的刀法、造型与题记书法会有紧密的联系。所以,理解造像题记书法只停留在拓本表面的浅层,而无法进入到文化底蕴的深层。从这点看,赵际芳的编辑观念就走到了当代的前沿,这也可以说是这本题记书法作品集的一大亮点。 不同载体呈现的造像题记书法 《咸同斯福》的第二大亮点是:呈现了不同载体的造像题记书法,让人看到了两者的差异与特点,从而为理解造像题记书法提供了新路径与新方法。 “龙门廿品”造像记作品集,实际是一种拓本,它以拓本(纸)作为载体。纸上拓出来的造像记书迹是白色的,而底则是黑色的。观者从拓本上看出来的圆笔、方笔,书与刻的种种问题,依据的都是纸上的痕迹。而《咸同斯福》上的造像记,除了拓本,还有原石(照相本,姑且称石本),即把石刻的原作照片同时刊出。如《郑长猷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等造像记均如此。石本造像记文字的线条、刀凿刻的痕迹清晰可见;起笔、收刀,点画的起止清清楚楚,各种细节展示无遗。所以,观赏这本作品集可以修正只看拓本造成的视觉偏差,书法史上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如书刻先后,方笔、圆笔是否写出来等问题,都迎刃而解。 如《郑长猷造像记》的“横”画,方笔落下,末端微微上翘,带有隶书的波挑,是写出来的。但拓本的“横”有时不清,甚至与石本相异。再如第二行第四字“亡”,拓本末端圆收,但石本末端微上挑,挑笔尖利。所以,石本、拓本传达的信息差异很大。比较而言,石本更接近书写时的原始状态。第二行的“父”“敬”“造”的捺脚,石本呈现出书写的意味,而拓本则没有,或很弱,粗看字形相似,细看则明显石本优,拓本劣。 《郑长猷造像记》以及《广武将军》等碑,沙孟海认为书刻俱劣;而康有为评《郑长猷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等“气象挥霍,体裁凝重”,为“沉著劲重”一体。 《郑长猷造像记》的书写体貌为隶楷,结体斜画收紧,正是魏碑体的特色。字画的搭配方式与唐楷完全不一样,像第六行的“女”及带“女”部首的“妾”等字,首笔的写法与楷法异,折笔后向右横行,这种结体方式反而天真有拙趣。再如“像”的右部三撇,撇笔都夸张平行左斜下,右部变成两点,形成对照,都显示出当时流行的魏楷的书写特色,故是写出来的,而经过刊刻的二次创作,三角形的点变得更为尖利。“为”的横折钩(第二行)横画书写时又有顿笔,形态上为三笔。刀刻时依形制凿,收刀含蓄,故如“写”出来一样,故《郑长猷造像记》刀传笔意十分出色。从今天的视角看,此石书刻俱佳,是上乘之作。《郑长猷造像记》中的竖钩,刀刻十分精微,并非只用切刀完成,轻微的转势传达精彩。而拓本,这种书写意味就相对少得多。 石本清晰地传达了石刻的走向、轻重、使转的过程,故也能让观者体会到什么是“二度创作”“刀趣”。刻碑的凿刀有多种,刀口也有大小、厚薄等区别。《尉迟造像记》的刀法十分精湛,故也忠于原作,“亡息”中“息”的下部三点是三种形态相异的尖锐的三角形,各种“点”的刀刻痕迹显然给人雄浑有力的感觉,这与拓本上的“点”的感觉不同。 《始平公造像记》是方笔的典范,结体是标准的斜画紧结,而它又是“龙门廿品”中阳刻的作品,所以刀法、刀趣在此件作品为突出。这篇造像记大多点画是方笔,故形态雄峻,但也有些圆笔的笔意被刀法很好地传达了出来,可见方笔、圆笔都是写出来的。由于此件造像是阳刻,刻每个字都像刻印章一样,需剔除线条以外的石料,因此不存在自由发挥的空间。石刻本清晰地传达出一段线条的起始是如何完成的。如后一行的“九月十四日”,都可清晰看到每一字的线条边廓线,都用双刀冲切完成,连“钩”的末端是如何传笔意的也很清楚,这在拓本上是一点也看不到的。 由此可见,这本作品集将拓本与石本同时呈现,无疑是编者的良苦用心,值得观者比较、玩赏。 关注民间书法的书写 《咸同斯福》造像记收录的作品有300余幅,除了“龙门十九品”以及一部分贵胄、高官的造像记以外,大量的是一般王族成员和下层普通平民的造像记。由于相关身份、文化修养不同,书写的水准差异很大,故有不同的风格呈现,所以这本作品集的第三大看点是关注民间书法的书写。 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书界认为“龙门廿品”是民间书法的体貌,稚拙天真,雄强遒劲。赵际芳、胡鹏则指出:“十九品”多数应为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所写。这一点很正确。而古阳洞里的下层平民百姓的造像题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书写。 北朝统治者虽说是少数民族出身,但任用的许多官员都是汉文化底蕴深厚的人。鲜卑族迁洛阳后,汉化的程度、速度惊人,二三十年之间,许多鲜卑族已完全汉化了。如齐郡王元“锐志儒术,游心文苑,访道充食,从义遗优”。《元造像记》的文字或许出自他自己的手笔。 《尉迟造像记》(495年)是穆亮夫人请人为儿子作的造像记,书写的人肯定是上流社会的书法高手。七年后穆亮去世,《穆亮墓志》也是该人书写。元姓皇室者去世后的墓志也都是书写精英们所写。《法生造像记》《元详造像记》《马振拜造像记》等题记均有圆笔,有锺、王笔法的遗意。古阳洞中造像大多没有署名,只有《孙秋生造像记》和《始平公造像记》有书者姓名。一为孟广达文,萧显庆书;一为孟达文,朱义章书。这种署名的人必定是当地的书写高手。能在古阳洞造像的人,也大多是当地有声望、地位的人。造像记中,有多块是许多人合资共造的。如《孙秋生造像记》是二百人等造像记,《高树解佰都三十二人等造石像记》《邑主马振拜等三十四人造石像记》均有“义邑”冠题。义邑造像是当时僧官制度的一种形式,故书写者一定是当地书写好的人。一般的比丘、比丘尼等也造像。家境贫穷的人,请不起精英书写,他们的造像记不但文字短少,造像的艺术水准都很低。 从造像记的文字看,文化官员写的造像记,文辞优美,别字也少,如《尉迟造像记》:“愿牛橛舍于分段之乡,腾游无碍之境。”这种华丽词采颇多六朝骈体文风的特点。而一般下层官员或平头百姓的造像题记,文辞简单、粗白,如《一弗造像记》:“太和廿年,步舆郎张元祖不幸丧亡,妻一弗为造像一区,愿令亡夫直生佛国。”句式、语气都符合一个无势、无地位之人的口吻。有些地位低下又贫穷的人,只署个名,如《邑子马保中题记》只写了“邑子马保中”五个字。 古阳洞中“十九品”以及位阶高一点的官员造像题记,大多是标准的魏碑体,笔法精湛,造的佛像也精美无比,并有拓本问世。而下层比丘、清信女的题记,造像粗糙,别字多,甚至连简单的字都写错。这种社会底层的题记,自然无拓本传世。而《咸同斯福》将这类无拓本的题记也一一展示,让今天的人能看到文化低下的平民题记的民间书风。这种题记或许不是书法爱好者的范本,却是书法研究者的重要参考框架,其价值不亚于优异的“十九品”。 平民百姓的造像题记,放在北魏迁都后的书法环境中,其字体也该是魏楷趋于成熟时期的状态,而题记中的民间魏楷却与文化精英的魏楷在体貌上还是有许多不同。斜画紧结的特征虽有,却并不纯正,结体中多自出异想。像《黑瓮生为亡妻造像记》(造像记号1968),“造”的“辶”为一竖与一斜横;“石”的撇笔从横的中部划出,封口一横则拉长出口;“区”字“匚”部下横左移至竖左,“品”写成上边“两口”下边一“口”,“为”字则有连笔。另一个《王婆罗门造像记》(造像记号1980),文“王婆罗门为亡母造像一区”分四列,前三列多三字,“一区”为第四行,“罗”在界格线上。其中,“为”完全是行书的形态,有连笔,“婆”字也有连笔。故知,平民造像记的字法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计笔顺的次序、装配的美观、刊刻之工拙。拙厚中有异态,很有书写性。《畅造像题记》中连“兄弟”的写法都不合常理。所以,如若没有见过真正的民间魏楷,将标准题记魏楷视为民间书风,则对当时的魏楷体貌理解就偏了。 所以说《咸同斯福》的编选,很有书法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值得观赏者细细品赏、辨认、思考。
咸同斯福 内容简介
古阳洞是北魏孝文帝迁都与文化改革所影响的一个洞窟,是北魏造像题记的一个高度。从皇家贵戚到地方官吏与庶民的造像题记,各有其艺术特点,但是历来对于龙门石窟造像题记的写与刻的问题,以及书写者身份问题众说纷纭。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探析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尤其是古阳洞造像题记书写者问题,有一定的意义。古阳洞平时不对外开放,观众无法近距离欣赏石窟中的造像题记,该书籍计划从古阳洞实际现场拍摄图版,结合拓本,给读者呈现出更为直观的欣赏方式,为书法学习者提供较好的参考资料。对于探析古阳洞造像题记的书法艺术具有一定帮助。
咸同斯福 节选
观赏造像记书法的新范本、新视角与新方法 楚默 赵际芳主编的《咸同斯福——古阳洞造像题记及书法艺术》是一本别出心裁、极富创新观念的书法作品集,它收录了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造像题记300余幅。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早开凿的洞,收录了*早的造像题记书法。著名的“龙门廿品”中十九品出自古阳洞,历来被视为魏碑的范本。“龙门廿品”被康有为列为必购之碑,集中体现了魏碑的精华;在本书之前,拓本不知印了多少版本。那么,赵际芳所编的这本《咸同斯福》是不是炒炒冷饭,重印一遍“龙门十九品”呢?显然不是。赵际芳曾是一名资深编辑,在《中国书法》杂志社工作十多年,阅过无数写经墨迹,也阅过无数魏碑真迹。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观念、视角全新的造像记书法作品集。该书之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将造像题记书法放在多维文化视野中呈现,并不是单一的题记书法拓片的再版 这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将造像题记作品放在一个具体的佛教文化、制度文化的背景中呈现。题记书法只是一端,更多的篇幅放在该造像题记的文化背景展示。一篇造像题记在古阳洞的什么位置,刻在佛像的什么地方,大小,佛像周围的各种图式、花纹,是弥勒像还是释迦牟尼像,胁侍菩萨什么状貌,胖瘦、姿态、手势、服饰纹路,等等,都有具体交待。也就是说,凡与题记书法相关的整个文化环境,能具体呈现的一律立体式加以陈列。古阳洞高大壮观,一则题记所占的空间其实很小,故将题记放在一个形象生动的佛教文化环境中,题记书法的佛教文化底蕴就得到生动展示,这无疑是一种题记书法展示的新方式。故是一种观念崭新的书法范本。 古阳洞中的佛教造像主要是释迦与弥勒像,因为北朝时流行的佛教信仰主要是信从弥勒佛和释迦佛。《牛橛造像记》称“造弥勒像记”,《郑长猷造像记》谓“为亡父等造弥勒像”;《元详造像记》造的都是弥勒佛像,《元燮造像记》造的都是释迦像,但仍有“二菩萨”。从题记看,发愿人要表达的也是弥勒经的思想。《牛橛造像记》《侯太妃造像记》表达的都是今世不旺、祈求来世昌盛的心愿。弥勒信仰尤适合下层民众,因为经文不长,容易背诵,修行方法简单。古阳洞中也有少量的观音像,那是以后才刻的。如《王仲和造观音像记》(公元521年)、《安定王为女夫闾散骑造观世音像记》,肯定是稍后刻的。 弥勒造像的刀法、造型也都不同于云冈石窟造像。云冈造像较多地反映出犍陀罗及印度艺术的特征,造像雄伟、体胖硕大,衣纹和装饰采用阴刻,是北魏早期的审美观。而到了龙门时代,弥勒和二胁侍菩萨面容清瘦,颈部细长,双肩消瘦,身体修长,形态清俊秀逸。这种崭新的造像风格也体现在《杨大眼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元详造像记》等造像中,显示出龙门造像的新形象,这都有赖于刀法的改进。 所以,观赏造像书法中的佛教文化底蕴,观看题记上方、左右的诸佛像,并不是多余的举措。《咸同斯福》正文**篇有一篇赵际芳与胡鹏的重要论文《从北魏制度的建立看古阳洞造像题记》。这篇论文提及“制度”,包括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僧官制度等。不理解这些制度的来龙去脉,也就很难解开造像题记书法的许多谜团。文中举例说:《孙秋生造像记》后增人名都以“唯那”开头,为僧官“维那”;古阳洞中地方官员、僧人造像题记的多少,都与一定的僧官制度、文化制度相关;不同地位的官员,不同技术的工匠都于造像题记书法字体、笔法、刀法有着明显的差异,可见镌刻受各种制度的制约是明显的。 平心而论,过去学习“龙门廿品”书法的人很少知道题记书法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也不知造像的刀法、造型与题记书法会有紧密的联系。所以,理解造像题记书法只停留在拓本表面的浅层,而无法进入到文化底蕴的深层。从这点看,赵际芳的编辑观念就走到了当代的*前沿,这也可以说是这本题记书法作品集的一大亮点。 孙秋生二百人等造石像记 不同载体呈现的造像题记书法 《咸同斯福》的第二大亮点是:呈现了不同载体的造像题记书法,让人看到了两者的差异与特点,从而为理解造像题记书法提供了新路径与新方法。 “龙门廿品”造像记作品集,实际是一种拓本,它以拓本(纸)作为载体。纸上拓出来的造像记书迹是白色的,而底则是黑色的。观者从拓本上看出来的圆笔、方笔,书与刻的种种问题,依据的都是纸上的痕迹。而《咸同斯福》上的造像记,除了拓本,还有原石(照相本,姑且称石本),即把石刻的原作照片同时刊出。如《郑长猷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等造像记均如此。石本造像记文字的线条、刀凿刻的痕迹清晰可见;起笔、收刀,点画的起止清清楚楚,各种细节展示无遗。所以,观赏这本作品集可以修正只看拓本造成的视觉偏差,书法史上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如书刻先后,方笔、圆笔是否写出来等问题,都迎刃而解。 如《郑长猷造像记》的“横”画,方笔落下,末端微微上翘,带有隶书的波挑,是写出来的。但拓本的“横”有时不清,甚至与石本相异。再如第二行第四字“亡”,拓本末端圆收,但石本末端微上挑,挑笔尖利。所以,石本、拓本传达的信息差异很大。比较而言,石本更接近书写时的原始状态。第二行的“父”“敬”“造”的捺脚,石本呈现出书写的意味,而拓本则没有,或很弱,粗看字形相似,细看则明显石本优,拓本劣。 《郑长猷造像记》以及《广武将军》等碑,沙孟海认为书刻俱劣;而康有为评《郑长猷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等“气象挥霍,体裁凝重”,为“沉著劲重”一体。 《郑长猷造像记》的书写体貌为隶楷,结体斜画收紧,正是魏碑体的特色。字画的搭配方式与唐楷完全不一样,像第六行的“女”及带“女”部首的“妾”等字,首笔的写法与楷法异,折笔后向右横行,这种结体方式反而天真有拙趣。再如“像”的右部三撇,撇笔都夸张平行左斜下,右部变成两点,形成对照,都显示出当时流行的魏楷的书写特色,故绝对是写出来的,而经过刊刻的二次创作,三角形的点变得更为尖利。“为”的横折钩(第二行)横画书写时又有顿笔,形态上为三笔。刀刻时依形制凿,收刀含蓄,故如“写”出来一样,故《郑长猷造像记》刀传笔意十分出色。从今天的视角看,此石书刻俱佳,是上乘之作。《郑长猷造像记》中的竖钩,刀刻十分精微,并非只用切刀完成,轻微的转势传达精彩。而拓本,这种书写意味就相对少得多。 比丘慧成造石像记(始平公造像)石本 石本清晰地传达了石刻的走向、轻重、使转的过程,故也能让观者体会到什么是“二度创作”“刀趣”。刻碑的凿刀有多种,刀口也有大小、厚薄等区别。《尉迟造像记》的刀法十分精湛,故也*忠于原作,“亡息”中“息”的下部三点是三种形态相异的尖锐的三角形,各种“点”的刀刻痕迹显然给人雄浑有力的感觉,这与拓本上的“点”的感觉不同。 《始平公造像记》是方笔的典范,结体是标准的斜画紧结,而它又是“龙门廿品”中唯一阳刻的作品,所以刀法、刀趣在此件作品*为突出。这篇造像记大多点画是方笔,故形态雄峻,但也有些圆笔的笔意被刀法很好地传达了出来,可见方笔、圆笔都是写出来的。由于此件造像是阳刻,刻每个字都像刻印章一样,需剔除线条以外的石料,因此不存在自由发挥的空间。石刻本清晰地传达出一段线条的起始是如何完成的。如*后一行的“九月十四日”,都可清晰看到每一字的线条边廓线,都用双刀冲切完成,连“钩”的末端是如何传笔意的也很清楚,这在拓本上是一点也看不到的。 由此可见,这本作品集将拓本与石本同时呈现,无疑是编者的良苦用心,值得观者比较、玩赏。 比丘慧成造石像记(始平公造像)拓本 关注民间书法的书写 《咸同斯福》造像记收录的作品有300余幅,除了“龙门十九品”以及一部分贵胄、高官的造像记以外,大量的是一般王族成员和下层普通平民的造像记。由于相关身份、文化修养不同,书写的水准差异很大,故有不同的风格呈现,所以这本作品集的第三大看点是关注民间书法的书写。 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书界认为“龙门廿品”是民间书法的体貌,稚拙天真,雄强遒劲。赵际芳、胡鹏则指出:“十九品”多数应为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所写。这一点很正确。而古阳洞里的下层平民百姓的造像题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书写。 北朝统治者虽说是少数民族出身,但任用的许多官员都是汉文化底蕴深厚的人。鲜卑族迁洛阳后,汉化的程度、速度惊人,二三十年之间,许多鲜卑族已完全汉化了。如齐郡王元“锐志儒术,游心文苑,访道充食,从义遗优”。《元造像记》的文字或许出自他自己的手笔。 《尉迟造像记》(495年)是穆亮夫人请人为儿子作的造像记,书写的人肯定是上流社会的书法高手。七年后穆亮去世,《穆亮墓志》也是该人书写。元姓皇室者去世后的墓志也都是书写精英们所写。《法生造像记》《元详造像记》《马振拜造像记》等题记均有圆笔,有锺、王笔法的遗意。古阳洞中造像大多没有署名,只有《孙秋生造像记》和《始平公造像记》有书者姓名。一为孟广达文,萧显庆书;一为孟达文,朱义章书。这种署名的人必定是当地的书写高手。能在古阳洞造像的人,也大多是当地有声望、地位的人。造像记中,有多块是许多人合资共造的。如《孙秋生造像记》是二百人等造像记,《高树解佰都三十二人等造石像记》《邑主马振拜等三十四人造石像记》均有“义邑”冠题。义邑造像是当时僧官制度的一种形式,故书写者一定是当地书写*好的人。一般的比丘、比丘尼等也造像。家境贫穷的人,请不起精英书写,他们的造像记不但文字短少,造像的艺术水准都很低。 高树解佰都三十二人等造石像记 石本 从造像记的文字看,文化官员写的造像记,文辞优美,别字也少,如《尉迟造像记》:“愿牛橛舍于分段之乡,腾游无碍之境。”这种华丽词采颇多六朝骈体文风的特点。而一般下层官员或平头百姓的造像题记,文辞简单、粗白,如《一弗造像记》:“太和廿年,步舆郎张元祖不幸丧亡,妻一弗为造像一区,愿令亡夫直生佛国。”句式、语气都符合一个无势、无地位之人的口吻。有些地位低下又贫穷的人,只署个名,如《邑子马保中题记》只写了“邑子马保中”五个字。 高树解佰都三十二人等造石像记 拓本 古阳洞中“十九品”以及位阶高一点的官员造像题记,大多是标准的魏碑体,笔法精湛,造的佛像也精美无比,并有拓本问世。而下层比丘、清信女的题记,造像粗糙,别字多,甚至连简单的字都写错。这种社会底层的题记,自然无拓本传世。而《咸同斯福》将这类无拓本的题记也一一展示,让今天的人能看到文化低下的平民题记的民间书风。这种题记或许不是书法爱好者的范本,却是书法研究者的重要参考框架,其价值不亚于优异的“十九品”。 平民百姓的造像题记,放在北魏迁都后的书法环境中,其字体也该是魏楷趋于成熟时期的状态,而题记中的民间魏楷却与文化精英的魏楷在体貌上还是有许多不同。斜画紧结的特征虽有,却并不纯正,结体中多自出异想。像《黑瓮生为亡妻造像记》(造像记号1968),“造”的“辶”为一竖与一斜横;“石”的撇笔从横的中部划出,封口一横则拉长出口;“区”字“匚”部下横左移至竖左,“品”写成上边“两口”下边一“口”,“为”字则有连笔。另一个《王婆罗门造像记》(造像记号1980),文“王婆罗门为亡母造像一区”分四列,前三列多三字,“一区”为第四行,“罗”在界格线上。其中,“为”完全是行书的形态,有连笔,“婆”字也有连笔。故知,平民造像记的字法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计笔顺的次序、装配的美观、刊刻之工拙。拙厚中有异态,很有书写性。《畅造像题记》中连“兄弟”的写法都不合常理。所以,如若没有见过真正的民间魏楷,将标准题记魏楷视为民间书风,则对当时的魏楷体貌理解就偏了。 所以说《咸同斯福》的编选,很有书法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值得观赏者细细品赏、辨认、思考。
咸同斯福 作者简介
赵际芳,哲学(书法)博士,艺术学(书法)博士后。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专职研究员,曾任《中国书法》杂志副主编。
- >
中国人在乌苏里边疆区:历史与人类学概述
中国人在乌苏里边疆区:历史与人类学概述
¥40.8¥48.0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实旅程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实旅程
¥19.3¥35.0 - >
我与地坛
我与地坛
¥16.8¥28.0 - >
二体千字文
二体千字文
¥23.8¥40.0 - >
月亮虎
月亮虎
¥15.4¥48.0 - >
新文学天穹两巨星--鲁迅与胡适/红烛学术丛书(红烛学术丛书)
新文学天穹两巨星--鲁迅与胡适/红烛学术丛书(红烛学术丛书)
¥9.9¥23.0 - >
中国历史的瞬间
中国历史的瞬间
¥12.5¥38.0 - >
唐代进士录
唐代进士录
¥26.7¥39.8
-
传世书法
¥10.2¥26.8 -
书法口袋书:礼器碑
¥5.2¥10 -
书法口袋书:赵孟頫 玄妙观重修三门记
¥5.2¥10 -
明清篆刻诸家-中国篆刻
¥21¥30 -
古鉨 官印 私印-中国篆刻
¥21¥30 -
王羲之书佛遗教经
¥21.6¥28
巴金:云与火的景象
¥11.6¥21.0山东馆藏文物精品大系山东馆藏文物精品大系:玉器卷
¥1248.0¥2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