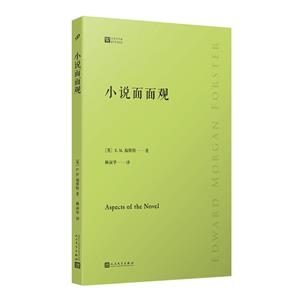-
>
我与父辈(九品)
-
>
商市街 回忆鲁迅先生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彩虹几度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古都·虹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舞姬·再婚者
-
>
碧轩吟稿
-
>
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第三辑)(全十五册)
小说面面观 版权信息
- ISBN:9787020179244
- 条形码:9787020179244 ; 978-7-02-017924-4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小说面面观 本书特色
《小说面面观》是福斯特唯一的文学论著,是从事小说写作、文学批评与赏析者了解了解小说艺术奥秘的必读经典,也是20世纪小说美学经典著作之一。在这本书里,福斯特把不同的作家作品放在一起比较,以找出各自的特点和共同的规律,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引领读者弄清小说创作中的一些奥秘。听起来是教人怎么写小说,实质上也是教人怎么读小说,因为正确的阅读是写作的前提。
小说面面观 内容简介
《小说面面观》是从事小说写作、文学批评与赏析者了解小说艺术奥秘的必读经典。 《印度之行》后,福斯特将重心转向了讲学与文学评论。1927年,他应邀到剑桥大学开设讲座,一系列演讲成为《小说面面观》的基础。全书共分九章,涉及小说的七个层面,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模式、节奏。福斯特认为,小说家的任务即是熟练地驾驭这些面向,做到“面面俱到”。 《小说面面观》是福斯特唯一的文学批评专著,是公认的20世纪小说美学经典著作。
小说面面观 目录
作者说明
一、导言
二、故事
三、人物
四、人物(续)
五、情节
六、幻想
七、预言
八、模式与节奏
九、结语
小说面面观 节选
不是那样的,小说家面对的难题就够多的了。今天我们就来仔细看看小说家解决这些难题所用的手段中的两种——直觉式手段,因为小说家创作中使用的方法和我们研究其作品时所用的方法相当不同。**种方法是运用不同类型的人物。第二种方法与视角有关。 一、我们可以把人物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 扁平人物在十七世纪被称为“谐趣人物”,有时也称为类型化人物,有时叫漫画式人物。就其*纯粹的形式来说,这类人物是围绕着单独一个思想或者特质来塑造的:超过了一个,人物就开始向圆形人物弯曲。真正扁平的人物一句话就可以体现出来,比如:“我是绝不会抛弃密考伯先生的。”这就是密考伯太太,她说她不会甩了密考伯先生就绝对不会,这就是她。还有:“我一定要掩盖这种状况,使个障眼法也行,不能让人看出主人家道中落了。”这是《拉美莫尔的新娘》中的卡莱布·鲍尔德斯通。他没这么说过,但完全是这样做的;除了这件事以外,他没有自己的存在,没有快乐,必然会让单纯的仆人特质变得复杂的任何私欲和痛苦他都没有。不论他做什么,不论他去哪里,不论他撒什么谎或者打碎了哪个碟子,都是为了掩盖主人家里的贫穷。这并不是他的固定观念,因为他脑子里没有让这种观念固定下来的地方。他就是观念本身,他所拥有的这种生命是从边缘发出光来的,小说中的其他元素碰撞的时候,他的生命与之相撞,就会发出闪烁的光。再看普鲁斯特的例子。普鲁斯特笔下有着众多的扁平式人物,比如帕玛公主,或者雷格兰丁。每一个都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帕玛公主的那句话就是:“我必须特别小心,要表现得充满善意。”除了特别小心,她真的什么也不做,书中比她复杂一点的人物都很容易看穿这种善意,因为那不过是小心谨慎的副产品。 扁平人物的一个大优点就是无论他们何时出现,都很容易认出来——读者是用情感之眼把他们认出来的,不是用视觉,视觉只会注意到某个名字又出现了。俄国小说中很少有这类人物,一旦出现,就会起很大的辅助作用。能调动全部力量一举达成目的对作者而言是件快事,扁平人物对他就很有用,因为这种人物绝对不需要重新介绍一番来历,也绝不会跑掉,不必费心去给他们编后续的故事,他们还自带气氛——一个个发光的小碟子,尺寸是预制的,可以在小说世界的虚空和星星之间像筹码一样推来推去。效果绝对令人满意。 第二个优点是,这种人读者看完书后很容易记住。他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坚定不移,因为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他们始终如一;他们经历过各种环境,这就让他们在读者的回忆中拥有了一种可以让人得到安慰的力量,他们得以诞生的作品也许会消亡,而他们会在读者的记忆中存留。《埃文·哈林顿》b 中的女伯爵就是个很好的小例子。我们来比较一下对她的记忆和对贝姬·夏普的记忆。我们不记得女伯爵做过什么或者经历过什么。记忆清晰的是她的形象,还有伴随着这个形象的那句口头禅,也就是:“我们以老父为荣,但是必须把他忘记。”她丰富的幽默感全都由此生发。她就是扁平人物。而贝姬是圆形的。她也唯利是图,但是没法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对她的记忆都与她所经历的那些大场景有联系,而且受到这些场景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不太容易记住她,因为她在不停地变,和真实的人一样是多面的。我们所有人,甚至那些久经世故的人,都渴望永恒,追求超凡脱俗的永恒是一件艺术作品存在的主要理由。我们都希望作品能够永存,成为避难所,其中居民的样貌恒久不变,这大概就是扁平人物存在的理由。 尽管如此,把目光严格锁定在日常生活上的批评家——像我们上周一样——几乎无法容忍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现人性。他们认为,维多利亚女王都无法用一句话来概括,密考伯太太怎么就可以?我们有位顶级作家诺曼·道格拉斯先生就属于这类批评家,我下面引用的他这段话以强硬的口气反对扁平人物。原文出自他写给戴·赫·劳伦斯的一封公开信,两人正在吵架:一对斗士笔战的激烈程度让我们感觉自己就像在高处的亭子里观战的一大帮淑女。他批评劳伦斯在一部传记里用“小说笔法”篡改事实,接着他对这种写法做出了定 义: 不得不说,这样做是由于没能认识到常人头脑的复杂性。作者以文学目的为由,只挑选人物的两三 个侧面予以表现,这些侧面通常是他们性格中*引人注目因而也是*有用的部分,而其他部分作者全都 无视。不管是什么性格特征,只要和所挑选的特质不相符就消除掉——必须消除,否则其描述就站不住 脚。这些和这些是素材:与之不符的一切都得扔到海里去。由此可见,小说笔法的依据虽然经常是符合 逻辑的,却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基础上:只取其所好而忽略其他。所选的侧面也许事实的确如此,但 是太少了:作者所说可能是真实的,却绝非全部真相。这就是小说笔法。它篡改了生活。 怎么说呢,按照这个定义,小说笔法用于传记自然是不好的,因为不存在人格单一的人。可是在小说中,这种写法自有其地位:一部原本就很复杂的小说常常既需要圆形人物也需要扁平人物,两者碰撞的结果比道格拉斯先生没有明说的那种主张反映生活更为准确。狄更斯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扁平的(皮普和大卫·科波菲尔是对圆形人物的尝试,可是写得缺乏自信,结果就把他们写成了像是美丽的肥皂泡而不是坚实的人物)。几乎每个人物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却依然能让人获得对人性深度的精彩感受。或许是狄更斯的巨大活力稍稍撼动了他的人物,他们借取了他的生命,似乎拥有了自己的生活。这就是个魔术戏法;我们随时都可以从侧面去看匹克威克先生,发现他不比留声机唱片更厚。可我们永远都看不清他的侧影。匹克威克先生太精明、太老练了。他看上去总是一副在掂量着什么的样子,他让人给锁进女子学校壁柜里的时候,就像在温莎给装进洗衣筐里的福斯塔夫一样笨重不堪。狄更斯的天分之一就是他真的用上了类型人物和漫画人物,这些人只要再度出场,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来,然而其效果却并不机械,对人性的观察也并不肤浅。不喜欢狄更斯的人自有其充分的理由。他本该是个很差劲的作家。实际上他是我们的一位大作家,他利用类型化人物获得的巨大成功说明,扁平包含的意义丰富,或许并不止限于严厉的批评家所承认的那一点。 我们再看赫·乔·威尔斯。大概除了《基普斯》(Kipps)中的基普斯和《托诺—邦盖》(Tono Bungay)中的婶婶以外,威尔斯的人物都扁平得像照片一样。但是这些照片被赋予了极大的活力,让我们忘记了这些人物的复杂性都是摆在表面上的,擦刮几下或者卷起来就会消失。威尔斯笔下的人物的确难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对观察要注重得多,并不生造类型化的人物。然而他的人物很少凭自己的力量活起来。是作者用自己灵巧而有力的双手摇动他们,让读者产生一种有深度的感觉。威尔斯和狄更斯这样出色但不完美的小说家非常善于传送力量。他们小说中富有活力的部分能够激发没有活力的部分,让人物活蹦乱跳,说话的方式也令人信服。这和完美的小说家大为不同。完美的小说家直接接触他所有的素材,他富于创造力的手指似乎触摸过每句话每个字,从内到外。理查森、笛福、简·奥斯丁在这一点上堪称完美,他们的作品也许够不上伟大,但是他们的手始终放在作品上,那门铃一摁就响,其间毫无阻滞,不像那些人物不在作者直接控制之下的作品。 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扁平人物写得成功并不像圆形人物那样属于重大的创作成就,而且扁平人物写得*好的都是喜剧角色。严肃的或者悲剧性的扁平人物容易招人讨厌。一露面就喊“报仇啊!”或者“我的心在为人类滴血!”或者什么别的套话,总会让人心头压抑。有一位当代通俗作家写的一部小说,中心人物是苏塞克斯郡的一个农夫,他老说:“我要把那块荆豆地犁出来。”农夫有了,地有了,他说要把地犁出来,他确实也犁了,可这句话却不像那句“我绝不会抛弃密考伯先生”,因为我们对他的执着简直烦透了,根本不会在意他是犁了还是没犁成。如果他的这句口头禅经过分析可以和人的其他七情六欲扯上关系,我们就不会感到厌烦了,因为那句话不再仅止于标示这个人,而成了他心中的一种执念,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从一个扁平化的农夫转化为一个圆形的农夫。只有圆形人物才适于表现具有任一时间长度的悲剧,让我们可以体验到除了幽默和得体以外的所有情感。 所以我们现在且放下这些二维的人物,把话题转向圆形人物,来看《曼斯菲尔德庄园》,看看带着哈巴狗坐在沙发上的伯特伦夫人。狗自然是平面的,就像大多数小说中的动物一样。书中曾写到这条狗无意中跑进一个玫瑰花圃,就像用硬纸板做出来的那种画面一样,但也仅此而已,书中大部分场景里,这条狗的女主人似乎和她的小狗一样,都是用同样简单的材料裁剪出来的。伯特伦夫人的口头禅是:“我是好脾气的人,但是受不得累”,她就是依此行事的。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祸事。她的两个女儿出事了,而且是奥斯丁小姐的世界里*为严重的事故,比拿破仑战争还要严重得多。茱莉亚私奔了;玛丽亚婚姻不幸福,也和情人跑了。伯特伦夫人是什么反应呢?描写这个场景的那句话很说明问题:“伯特伦夫人没有细想,但是在托马斯爵士的指点下,她很冷静地把所有的重点都捋了一遍,于是从事情的严重程度中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她既不勉强自己,也不要求范妮给她出主意,很少去想罪过啊耻辱啊什么的。”这些词分量都很重,我原来看到这里就有些担忧,觉得简·奥斯丁的道德感要失控了。她可以而且毫无疑问也确实下手抨击了罪过和耻辱,她理所当然地让埃德蒙和范妮在心里感受到了所有可能引发的痛苦,不过她有权搅扰伯特伦夫人始终如一的清净吗?这不就像是给哈巴狗儿三张面孔,派它去守地狱的大门?难道这位夫人不是应该坐在沙发里不动,只是说“茱莉亚和玛丽亚的事真是又可怕又伤神,不过范妮到哪儿去了?我又掉了一针”? 我原来的这些想法其实是误解了简·奥斯丁的方法,正像司各特对她的误解一样,他曾经祝贺她能在一方象牙上作画,长于精描细写。她的确是微型画的一把好手,但她的作品绝不是二维的。她笔下的人物都是圆形的,或者说具备成为圆形人物的潜力。就连贝茨小姐都是有头脑的,就连伊丽莎白·艾略特也是有心肠的,伯特伦夫人的道德热情不再让我们迷惑,因为我们发现,小碟子突然扩展,变成了一个小圆球。小说结尾时,伯特伦夫人又回归扁平,这是真的;她给读者留下的主要印象的确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但这并不是简·奥斯丁对她的构思,她露面总有新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什么奥斯丁的人物每次出现都会给我们带来一点新的快乐,不像狄更斯的人物带来的是重复的快乐?为什么他们在交谈中融合得如此之好,引出彼此却天衣无缝,从不刻意表演?这个问题可以有好几种回答:比如说她不同于狄更斯,是个真正的艺术家,或者说她从不屈尊于塑造漫画人物,等等。而*好的回答是,和狄更斯相比,她写的都是小人物,但是这些人物组织得很好。他们的功能是全方位的,书中情节对他们的要求再高一些,他们也能做到。假设路易莎·穆斯格罗夫在科布摔断了脖子吧。对她死亡的描写很可能绵软无力,一副淑女腔调——对暴烈行为的描写远远超出了奥斯丁小姐的能力——但是尸体抬走以后,其余人的反应马上就会恰如其分,而且会展示出他们性格中新的一面,《劝导》作为一部小说可能因此就毁了,我们却可以对温特沃斯上尉和安有比现在更多的了解。奥斯丁所有的人物都可以随时扩展人生,去过她的小说规划中很少要求他们去过的生活,所以他们才活得如此真实可信。我们再回头来看伯特伦夫人和那句很说明问题的话。看看这句话是如何以微妙的方式从她那句公式化的口头禅出发进入了一个公式不起作用的领域。“伯特伦夫人没有细想”。非常准确:公式都这样。“但是在托马斯爵士的指点下,她很冷静地把所有的要点都捋了一遍”。托马斯爵士的指点也是她那个公式的一部分,仍然存在,不过在这里推动着这位夫人走向一套独立而且意外的道德观念。“于是从事情的严重程度中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这就是道德强音——非常响亮,但是出现的时机经过了精心安排。接下来是一个十分巧妙的弱音,以几个否定的形式出现:“她既不勉强自己,也不要求范妮给她出主意,很少去想罪过啊耻辱啊什么的。”她的公式再次出现,因为按照习惯她确实是要把麻烦降到*低程度,确实是要求范妮给她出主意说说该怎么办,十年来范妮所做的事也的确就只是给她出主意。这些词语用的是否定式,却起了提醒的作用,我们又看到了她的常态,一句话之间她就饱满起来,成了个圆形人物,然后又瘪了下去,回到了扁平状态。简·奥斯丁太会写了!寥寥几笔她就扩展了伯特伦夫人的维度,同时提高了玛丽亚和茱莉亚私奔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我说可能性是因为私奔属于暴烈行为的范畴,如前面所说,简·奥斯丁写这种事总是绵软无力,一副淑女腔调。除了她少女时代写的小说以外,她不会正面描写灾难。所有暴力一点的事都必须发生在“后台”——路易莎受伤和玛丽安·达什伍德生白喉病*接近于破例——这样一来,所有关于私奔的评论就必须写得真诚可信,否则我们就会怀疑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伯特伦夫人的反应使我们相信她的两个女儿真的跑了,而且她们必须跑,否则范妮就没有什么妙用了。不过是一个小关节,一个小句子,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高超的小说家如何巧妙地把她的人物调整为圆形。 纵观她的作品,都可以发现这种人物,表面上十分简单、平面,从来不需要多说,却也从来没有失了深度——亨利·蒂尔尼、伍德豪斯先生、夏洛蒂·卢卡斯,皆是如此。或许她给笔下人物贴上了“理智”“傲慢”“情感”“偏见”这样的标签,但是这些人物并没有束缚于标签上的这些特质。 至于何为圆形人物,从以上内容里已经可以看出其定义,没有更多要讲的了。我要做的只是从作品中找出一些我认为属于圆形人物的例子,以便我们对这个定义做后续的检验。 《战争与和平》中所有的主要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有的人物,普鲁斯特作品中的部分人物,比如家中那位老仆人、盖尔曼公爵夫人、德·查鲁斯先生、圣卢;包法利夫人和摩尔·弗兰德斯一样,同名作品中只讲她一个人,可以无限扩展其维度为自己所用;萨克雷作品中的部分人物,比如贝姬和比阿特丽克斯;菲尔丁作品中的部分人物——帕森·亚当斯、汤姆·琼斯;夏洛蒂·勃朗特作品中的部分人物,特别是露西·斯诺。(还有很多,这可不是一份目录大全。) 对圆形人物的检测方法就是看他能不能以可信的方式给人以惊讶的感觉。如果其言行举止从来不会让人吃惊,这个人物就是扁平的。如果他让人吃惊的方式不能令人信服,那他就是个装成圆形人物的扁平人物。圆形人物的身边是无法估量的生命力,也就是一部作品书页之间所蕴含的勃勃生机。作家使用圆形人物有的时候是单独用,更多的时候是和其他类型的人物结合起来用,通过圆形人物,小说家得以达成适应环境的目的,让人类和作品的其他方面和谐相处。
小说面面观 作者简介
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1879—1970),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作品包括六部小说,两集短篇小说集,几部传记和一些评论文章。其作品语风清新淡雅,描写的都是二十世纪初英国的社会状况,尤其长篇小说几乎都是反映英国中上层阶级的精神贫困,在每部作品中主人公都试图通过挣脱社会与习俗的约束来求得个人解放。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庄园》《印度之行》以及文学论著《小说面面观》等。他曾22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最终没有获奖,但已经证明了E.M.福斯特是20世纪伟大作家之一。
- >
【精装绘本】画给孩子的中国神话
【精装绘本】画给孩子的中国神话
¥20.9¥55.0 - >
朝闻道
朝闻道
¥20.2¥23.8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实旅程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实旅程
¥19.3¥35.0 - >
经典常谈
经典常谈
¥17.1¥39.8 - >
推拿
推拿
¥12.2¥32.0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装共3册
小考拉的故事-套装共3册
¥35.4¥68.0 - >
我与地坛
我与地坛
¥16.8¥28.0 - >
回忆爱玛侬
回忆爱玛侬
¥10.5¥32.8
-
老舍谈写作
¥9.3¥29 -
1900-2000-现代中国文学史精编
¥22.4¥56 -
人间词话
¥10.2¥26.8 -
语文杂记
¥28.5¥38 -
西南联大文学课
¥24.9¥58 -
类人孩:《动物庄园》另类解读
¥8.4¥28
苏州评弹艺术家评传 (五)
¥39.4¥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