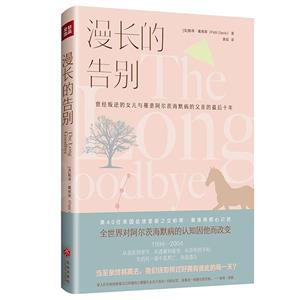-
>
(精)泰晤士哈德逊世界艺术巡礼:莫奈+高更+透纳(全三册)
-
>
张路江:一个人日常叙事的尊严
-
>
(精)梵·高手稿(花口本)
-
>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全四册)
-
>
寻觅凡·高:追随大师的艺术之旅
-
>
股票作手回忆录
-
>
南宋江西籍进士考录(全2册)
漫长的告别 本书特色
1.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小的女儿帕蒂·戴维斯倾心记述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的*后十年 帕蒂·戴维斯,里根*小的女儿,曾因政见不同与家人决裂,以叛逆的行径震惊世人。因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她与父亲和解,重回家庭,与家人共同开启了一段漫长的告别旅程,并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陪伴父亲的日子,以及童年记忆里与父亲、与家人的弥足珍贵的共处时光。 2. 关注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医学难题,直面每个成年人不可避免的心理挑战 平均每3秒钟全球就会产生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我国目前有1000多万患病人群,关心和照护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课题。 面对父母至亲终将老去的现实,我们该如何珍惜与之相伴的每一天?当那一天终将到来时,我们该如何与他们好好告别,又该以怎样的态度继续以后的生活? 3. 内容与形态双重匠心打磨,绝版十年后的再造与升级 特邀擅长文学翻译的译者精心重译,亲人间的温情与细腻柔软的力量氤氲纸上。文本经译者与编者数次推敲打磨,力求还原原著之精髓。 形态与内容珠联璧合,书名字体仿阿尔茨海默病做“渐退”设计,封面上的马、橡树、风筝等象征着作者记忆中与父亲一起度过的珍贵时光。 4. 全世界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因里根总统而改变 过去人们对阿尔茨海默病毫无概念,这种状况因里根而发生了改变。里根被确诊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后,就向社会公开了自己的病情,以自己的知名度唤醒全世界对这种病的关注,并在1995年成立了里根和南茜研究所,专门研究这种疾病。
漫长的告别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回忆录, 作者以日记的形式, 回忆了她与父亲从前的美好时光, 搜索了所有对父亲的记忆, 再一次触摸他, 聆听他的声音, 栩栩如生地重现了父亲的可亲可敬, 字里行间流露出女儿对父亲*真挚的爱与不舍。作者笔锋简洁流畅, 坦城感人, 字里行间中展现出了内心的炽热情感和夹杂着震惊、无助的心绪的错综复杂的百味人生。
漫长的告别 目录
1995 年4 月 / 希望的光芒
1995 年5 月,洛杉矶 / 死亡:生命永恒的伴侣
1995 年6 月 / 一次重生之旅
1995 年6 月末 / 面纱
1995 年7 月 / “漫长的告别”
1995 年7 月末 / 伟大的爱情
1995 年8 月,洛杉矶 / 父爱如山
1995 年8 月 / 失落、恐惧、成熟
1995 年9 月 / “只要我还能说话”
1995 年10 月 / 充满情感的心脏
1995 年10 月末 / 定格在心中的画面
1995 年11 月 / “我已经八十四岁了”
1995 年11 月,洛杉矶 / 平静之下的巨大力量
1995 年12 月 / 梦境
1995 年圣诞假期,洛杉矶 / 河流与牧场
1996 年1 月 / 阴沉的世界
1996 年2 月,洛杉矶 / 苦涩的甜蜜
1996 年3 月 / 你将如何度过*后的日子
1996 年4 月 / 爱的纽带
1996 年4 月,洛杉矶 / 牧场里,他无处不在
1996 年5 月 / 里根图书馆
1996 年7 月,洛杉矶 / “就像在和云彩说话”
1996 年7 月 / 刻在照片中的记忆
1996 年8 月 / 失去牧场,父亲缺席
1996 年10 月 / 他正在慢慢离去
1997 年2 月,洛杉矶 / 活在当下
2004 年6 月3 日 / 月圆之夜
2004 年6 月4 日 / 那一刻已经近了
2004 年6 月5 日 / 他从未离开
后记
漫长的告别 节选
1995 年7 月 “漫长的告别” 与所爱之人道别, 那句再见,不仅是道给即将离开的人, 也是道给他在人生旅途中积攒下来的点点滴滴。 阿尔茨海默病缓缓夺走一个人生命的过程被我的母亲称为“漫长的告别”。这是她公开发表过的少有几句评论之一。面对论及我父亲健康状况的话题,我们一致选择了用毕恭毕敬的沉默来掩饰。这是一种令人心碎的说法。她告诉我,自己再也不会重提这句话了,因为它催人泪下。 我刚刚结束《天使不死》的巡回售书活动,没有多少时间顾得上流泪。在飞机和陌生的酒店房间中,我一有空就睡觉,在根本没有机会整理的行李箱中飞快地东翻西找,从一个采访奔赴另一个采访。绝大多数采访都是友好的,充满了鼓励的意味。成为一名作家、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是我的选择。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历次的巡回售书“战役”中是如何幸免于难的。可以想见,即便是*顺利的巡回售书活动,也总会有一场采访令你对采访者的粗鲁迷惘地摇头。 事情发生在一座小城市里。城市的名字我就不提了。那是一场午后的脱口秀节目。节目主持是一个想成为却永远成不了奥普拉的女人。她开口询问了我父亲的状况。针对这个采访问题,我的答案一成不变。“他很好。”我说,“在涉及他健康状况的问题上,我的家人需要保留隐私。不过他很好。” 这样的答案通常就已足够,谁也不会进一步逼问。“那他还记得你吗?你能和他对话吗?”她显然认为,问几句我已明确表示不会回答的私人问题是完全合理的。 “如我所言,我们需要保留隐私。我觉得我们有这个权利。” “你们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现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是不是开始注意到他会忘东忘西,或是把事情搞混?” “我已经明确说过了,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我的语气更强硬了。我能感觉到现场观众的尴尬。她却又试了一次。 “现在和他对话是什么感觉?你都会和他聊些什么?” “这是我第四次也是*后一次给出同样的答复了。我们需要隐私。无论你用多少种不同的措辞问相同的问题,我都不会回答你的。” 观众鼓起掌来。她终于把话题转移到了另外一系列的问题上。 节目结束后,当我急匆匆地走向出口时,她开口说道:“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只不过是在尽一名记者的责任。” 我想我没有搭理她。 巡回售书的另一个难处虽然有些悲哀,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甜蜜的。一次又一次,在谈及父亲和我为他写的书时,我都会沉浸在记忆的荣光中,想起他忠实的信仰和讲过的故事中饱含的精神食粮。“漫长的告别”这句话时常在我的脑海中低语,如同一缕清风穿过敞开房门的屋子。我想流却没空流的眼泪在心里积成了一汪池水—耐心等待我靠近、深不见底的池水。回到纽约,我一心只想睡觉和哭泣。 在某种程度上,这趟巡回售书让我能够直面自己迄今为止的生活,直面自己过去的选择,直面我与父母经年的斗争。采访前,我会在演员休息室给母亲打电话,或是在酒店房间和机场里拨通她的号码。她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我还是能够看到,那些年的放逐如同荒原般在我的身后铺展开。 名望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即便你是伴随它长大的,也还是会被它惊得目瞪口呆。你以为自己已经对它了若指掌,能够按顺序安排好轻重缓急,思维清晰地做出选择,但大多数人都会犯错。我觉得聚光灯**次照在你身上的那一刻才是*重要的。没有哪个错误能比那一刻犯下的错误更加严重。它是个黄金时刻,并且永远不会重来。其他的时刻还会到来—我不相信我们只有一次机会能把事情做好—但永远不会再那般纯粹、毫无负担。 父亲当选总统那年,我28 岁。尽管对人们强烈的关注并不陌生,但我们还是陷入了媒体的旋涡中。显然,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父亲,我们其余的人也处在了聚光灯下。我犯下的**个错误就是以为自己能够应付一切。要是我能多一些犹豫,少一些笃定,就能多提几个问题,思考更多的选项。结果,陪伴我前行的却是对自身政治信仰极度的热诚。我曾在大型反核集会上发言,接受采访,把自己塑造成了父亲的政策*引人注目的反对者之一。要是我能多一些外交手段,少一些尖锐的言辞,其实本可以成为父亲与自由主义观点之间的桥梁。相反,即便是在那些与我持相同政治信仰的人眼中,我也不过是个愤怒的女儿。 宣泄完*初的愤怒,我又开始表达更加私密的情感,把在全世界面前展示我家庭的创伤视为己任。我的怒火招致其他人的愤怒。说我收到过恐吓信,那是轻描淡写。 这些问题大多是在巡回售书的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我其实很难摆脱自己的过去。每个人都在成长、转变和学习,但在公众的瞩目下经历这一过程会更加艰辛。大多数人都是宽容的,但我能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记忆是长久的。这就是在公众的目光中成长的难处:你永远处在别人对你的记忆之中。 在我的想象中,我会和父亲谈论此事,告诉他我多希望自己当初能以不同的方式去应对发生过的一切。也许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针锋相对的观点可以是一种启示,而不是一场战争。在我的想象中,他的眼中闪烁着光芒,微笑地说着“我很高兴我们现在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了”之类的话。然而这段对话只能发生在我的想象之中。在现实生活中,他身上可以参与对话的那一部分已经远去了。 碰上阿尔茨海默病之类的疾病,荒凉的感觉也会属于患者的朋友和爱人—那些见证了过程还要被丢下暗自神伤的人。你会眼睁睁看着一个人退到某个陌生的地方,心知自己无法跟上。失去他,你将一个人在荒野中徘徊,耳边回响着山坡上传来的回音。那只是回音—声音传来的地方越来越安静—于是你会更加仔细地聆听。 如今,母亲的很多话都是以“我记得……”开头的。 你之所以会为自己的记忆注入生机,是因为就在那里、就在你的眼前,坐在他过去经常坐着的椅子上,或是走在楼道里,抑或凝视窗外时,你都会想起往事。记忆被抹除后,剩下的就是一片空白,因此,每当想起某些画面或是只言片语,你都会欣然接受,紧紧抓着它们,拂去上面的灰尘,期待它们能永远鲜活。 现在,我时常想起父亲讲过的故事,希望能再听到他讲故事的声音,看到那双可以激活孩子的想象力、闪烁着喜悦光芒的蓝色眼睛。但我只能依靠回声来滋养自己。我想要他再告诉我一次,鹰与秃鹫的区别。它们的飞行轨迹、翅膀存在细微的差异。其中一种在朝猎物俯冲前会多盘旋一会儿。我过去常把它们弄混。要是我们在牧场上发现了二者中的任何一种,他就会耐心地为我一遍遍解释说明。我还是会把它们弄混,但我已经不能再问他了,因为他也记不得了。我想和他骑上马,朝着翠绿的山坡飞驰,可他已经永远无法再骑马了。 一次,在前往牧场的途中,车子正沿着穆赫兰道行驶。他停下车,对山坡上的一个男人说,他正在采摘的蓝羽扇豆是受保护植物。父亲解释得彬彬有礼,于是那个男人从山上爬了下来,手中却仍攥着非法采来的花朵。父亲相信,只要有可能,鲜花和野生动物都应该留在它们的应属之地。我五岁那年便能认出响尾蛇,知道要绕一个大圈才能躲开它们。我还知道,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对不能杀害一个生命。 我从未如此深切地渴望过童年—哪怕只是尝上一口,都如舌头上的威化饼,成为我与已然失之交臂的过去甜蜜的交流。成年人会带着可悲的智慧回首往事,想起儿时的我们是何等幸福,根本不知道人生在迈着坚定的步伐前进,也不知道岁月在倒数计时,仿佛时间不可能在我们的肉体上刻下痕迹。蓦然回首,我们才希望自己能够更好地把握某些时刻,久久凝视某个人的面庞或是壮观的夕阳,更仔细地聆听某个终有一日会归于沉寂的声音。我们还希望自己走得再慢一些,徘徊得再久一点儿,踏上不同的道路。我们将大大小小的往事储存在记忆中,期盼它们不会破碎或褪色,因为它们是我们活过这一世的见证。 与所爱之人道别,那句再见,不仅是道给即将离开的人,也是道给他在人生旅途中积攒下来的点点滴滴。我的父亲正迈着坚定的小步远离曾经的自己。我不知道还能从他身上学到什么东西—有关土地、马儿、鸟儿的飞行轨迹,还有只能在某些区域茁壮成长的植物。在牧场的橡树林里,他曾找到过一种打湿后会像肥皂一样起泡的植物。 他相信,要让孩子们为生活中的灾难做好准备,否则这些波折和突变有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结果。他会为我们设定几个情景,问我们打算怎么应对,然后温和地纠正我们。这样一来,就算灾难降临,知识也能成为我们的盟友。 有一次他问我:“如果你的卧室起火,房门却被堵住了,你会怎么做?” 看过无数电影的我回答:“我会冲破房门。” “那你就没命了。”父亲冷静地回答,“你刚走到距离火苗不到两英尺的地方,就会被热气灼伤肺部。” “那我就打破玻璃,跑到院子里去。” “好的。”他点了点头,“你怎么打破玻璃?” “用一把椅子。” 我总是能够清楚地分辨出,课程*重要的一部分何时到来。父亲会俯下身,用缓慢而谨慎的语气对我说话,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话能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你可以拿出一只抽屉,把它从窗户里推出去。”他告诉我,“这样就能形成一个整齐的缺口,不会在你爬出窗户时将你割伤。” 他让我为火灾、空袭警报和地震都做好了准备,却没有让我准备好失去他,没有给我工具去应对满腔悔意的冲击。我后悔自己厌恶他的那段时光,后悔曾甩掉他伸出的手,选择了如矛刺般尖锐的言语。那些都是深埋在我心里的记忆。如果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那么我还没有找到。 失去父亲或母亲的故事中通常都包含着发现的过程。打开一只抽屉、一本书、一盒信,你便能知晓从前并不了解他们的地方。他或她在喜欢的书本空白处潦草地写下想法,或是你无意中发现某封信。有些时候,我们是在父母去世后才了解他们的。我的母亲一直在收拾抽屉—我想,她应该是有意这么做的,因为她知道我们的生活有一部分是公开的,要面对全世界窥探的目光。她想要知道别人会发现什么。在父亲的其中一只抽屉里,她找到了给我的一封信。那是一份草稿,尚未寄出,是在我的自传出版前写下的。信中,他表示自己被我的怒火伤透了心,也表达了家庭和解的愿望,还有他对更多美好时光的记忆。信的开头,他写道“随着我年近八十一岁……”然后又划掉了自己的年龄,在上面写了一行“如今我已经八十一岁了……” 我想象,在日子缓慢流逝的过程中,他也许曾无数次拿出这封信,感觉自己的生命已所剩无几。我永远都无法知道他多久便会把它拿出来添上几笔,再重读一遍,也不知道他为何永远不曾将它寄出。在信的末尾,他写道:“求你了,帕蒂,别带走我们对那个真心疼爱、心心念念的女儿的回忆。” 如今,这封信已经被放进了我的抽屉,陷入了无边的沉寂。我多希望自己能和他聊一聊它,然而他对它的记忆可能已经消失在了地球的边缘。 人们离世时都会带走自己隐藏的秘密—烛光闪烁的欢乐记忆、支离破碎的悲伤记忆。他们离开了,记忆也将随之而去。我们剩下的人则会被丢在黑暗中,怀抱着再也没机会提出的问题,和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语。因为我们来得太迟了。 讲述这场“漫长告别”的任务已经落在了我的身上。尽管这些日子并不沉重,却还是需要被记录下来,因为它们珍贵万分。我们跨越苦痛去寻找救助,双手如同伸向圣杯,充满渴望。我们碰不到它,却知道它的存在。我还精进了忍住眼泪这门艺术,像只骄傲的野兽,将泪水储存起来,然后退回我的洞穴,好给它们应有的地位,尊重其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段漫长的旅程就是曾经似乎缝合在一起的确定性—我们在另一个人身上了解到的一点一滴—逐渐分崩离析的过程。你会习惯这样的疾病带来的惊喜,习惯那些令人困惑的短语,习惯突如其来的转折。你不指望什么,但已经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更加自如地呼吸。这将永远是一场等待的游戏。 即便没有疾病带来的并发症,对于年逾八十的人来说,人生的隧道也越来越窄。多年前,父亲在给我写信时就已经有了这种感觉。有些时候,我很想知道事情会在何时发生,我何时才会得到消息。半夜吗?黎明吗?无论是什么时候,我都十分清楚,父亲的离去将是一段平静的旅程。 昨天,我在针灸师的床上睡着了,身上各处经络上插着活血化瘀的针,坠入了漆黑一片的深度睡眠中,身陷紧张得令人心惊肉跳的鲜活梦境。我看见父亲从身体里迈了出去,离开八十四岁的自己,成了一个更加年轻、更有活力的男子,脸上还带着灿烂的微笑。他生龙活虎、热情洋溢地张开双臂,走向我的母亲,安慰她一切都会好的。 尽管一切终将有所不同,但都会归于平静。摆脱了悲伤、恐惧与无情的苦痛,生活将进入某种模式。就眼下的情况而言,生活就是等待。这就像是在闪电后数秒,等待你知道必将到来的雷鸣,试图预测风暴还有多远。
漫长的告别 作者简介
帕蒂·戴维斯(Patti Davis),原名帕特里夏·安·戴维斯·里根,美国前总统里根最小的女儿,里根与南希·里根WEIYI的女儿,演员,作家,模特。著有《我的视角》《天使不死》。她的许多文章被刊登在《时代》《新闻周刊》《时尚芭莎》《名利场》《城乡之间》《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上。 帕蒂·戴维斯曾经以叛逆著称,以各种出格的行为与父母对抗,就连帕蒂·戴维斯这个名字也是她为了抹去父亲和家族的烙印而取的艺名。
- >
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
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
¥13.8¥32.0 - >
中国人在乌苏里边疆区:历史与人类学概述
中国人在乌苏里边疆区:历史与人类学概述
¥40.8¥48.0 - >
中国历史的瞬间
中国历史的瞬间
¥12.5¥38.0 - >
月亮与六便士
月亮与六便士
¥13.4¥42.0 - >
烟与镜
烟与镜
¥18.2¥48.0 - >
诗经-先民的歌唱
诗经-先民的歌唱
¥15.1¥39.8 - >
莉莉和章鱼
莉莉和章鱼
¥16.0¥42.0 - >
大红狗在马戏团-大红狗克里弗-助人
大红狗在马戏团-大红狗克里弗-助人
¥3.3¥10.0
-
居里夫人自传
¥11.2¥35 -
弗洛伊德自述
¥7.5¥22 -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自传)
¥12.7¥39.8 -
在中国二十五年:上海《密靳氏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回忆录
¥18.4¥36 -
鹏程问道
¥19¥45 -
随遇而安(新版精装)
¥19.9¥49.8